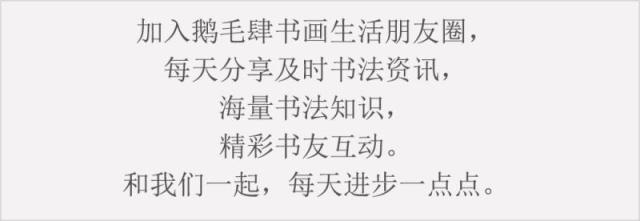周汝昌谈书法(三)
2016-05-19 10:42:01 来源: 点击:
(18)关于书法的几个比喻
(一)“篙师行船”是说将篙对着行船方向倒插下去,用臂抵篙,用腿蹬船。他加一个力给篙,从篙得到一个反力,传给了船,船从此力为正力,又与水的阻力来“斗争”,这样斗争着前进,在他身上正是兼着两对矛盾的力的对立统一。此一比喻,确实很妙。
(二)“担夫争道”,担夫争道的比喻比起篙师之理似乎更妙,担夫所用的“劲头儿”,一个是担子向下重压他,他得挺起腰板来往上“顶劲儿”,才能起立,一个是他还得挑着这个重量往前走,而不是立在原地练“内功”。这正有点像“勒”笔,横笔立下,而又要行笔。
担夫荷着重前进,绝不能学“读书人”踱着“八字步”以行,又绝不能像运动员“跑百米”拼命狂奔,他只能放快步、速度均匀的走起来,只有这样,担子才能和谐的颤起来,肩上的负荷最轻。在这样行进时,最怕阻碍,把步法速度打乱,负荷马上加重,他必须“争路而走”。在这种两个力交互地“斗争着”前进的当中,书家看到了、悟到了:又要行笔而又不是滑拖的劲头儿与此有相似之点。
(三)“折钗股”:这个比喻来自古代妇女的发钗,钗有两根股,折断了,钗股的折痕处,不论是平齐或斜断,都是方棱立角,显得锋利,绝不会有圆浑的断痕出现,用这来比方笔画的行笔遒劲,住笔峻洁。
(四)“锥画沙”:这是另一则极关重要的比喻,说到“锥画沙”要先说一下“藏锋”之说。世俗的“藏锋”大致有两种,一是“水平”说,一是“转圈”说。两者都叫人下笔就得把锋尖“裹”在笔画内,不许少露。就是我们常说回锋,比如锋尖原要右行的,先左行一下,再回来行笔;反之亦然。“转圈”说,是起笔收笔,锋类都要折叠回转一番,弄成一个“圆三角”,把锋藏起来,这样必须使每一画的两端都形成了一个不圆不角的墨疙瘩。以这为正法,违之为错。
而“锥画沙”之中的“藏锋”,是指在沙洲之地,平净细润之处,在这种细泥上用如锥的“利锋”去画字,其笔画是格外的清晰明快,而不是模糊浑沦、权桠龃龉。这种笔画全由利锥深画,锋入细泥。锋既深入,画方“沉著”,不是平拉滑拖,这个才叫“藏锋”。
宜兴紫砂陶器,往往刻有字画,高手所为极可赏爱。一般为紫砂做成生坯后,候干湿度合宜之时,用尖竹片或其它“利锋”,在上面写字绘画而成。这正是“锥画沙”的绝妙例证。
高手所刻,简直就是极好的字画,笔法一一具备。也有不会使工具、只会用“中锋”刻出花纹的,匀整如一,毫无笔法之意,便觉索然寡味。只要你有一点书法审美感,一眼便能看出。
(19)关于风格应如何学习
关于风格是一个复杂的问题,每个人都可心选取自己喜欢的来做借鉴,但正同“文如其人”,也是“字如其人”,风格实际上不能也不应学得“一模一样”,可以乱真的,就成了假古董,书法上的模仿,是初学的必要手段和步骤,而不是最终的目的,要吸取养分,培养自己的新风格。
(20)关于字体的“芒角”
“芒角”在中国书法史上的关系非常重大,夸张一点讲,书法史就是一部“芒角得失史”。
古代无法拍照,真迹易毁,书法痕迹全靠金石铸刻保存流传,千年的风日剥蚀,百世的人工槌拓,最先损伤、模糊、泯灭的就是“芒角”。
“芒角”一失,不但神采先损,连面目有时也会全非。
(21)关于世传《兰亭序》的辨伪
古代珍贵书迹,经过几次大规模的浩劫,剩余者已寥若晨星。到五代、南唐,仅有孑遗,宋朝统一,由南唐收来几项宝物。其中书法珍品,一是王羲之兰亭序石刻本,一是以二王为主的零碎六朝墨迹(有真有伪,有原迹有摹本)。前者,后来称为“定武本”兰亭,后者编集摹刻木板本,叫做淳化阁帖,由于极为宝贵难得,两者都被翻刻到无数次,几近“化身千亿”。
翻刻,首先最易失的就是“芒角”。
前者被“翻”得距离王羲之的十万八千里,后者被“翻”得简直就是“面条儿”和毫无生气的“蛇蚓”,令人啼笔皆非。
《定武兰亭》本来摹刻就是出于拙手,去真很远,又年久剥蚀,锋芒棱角尽失,原不足学,可是从北宋到南宋,却被奉为无上至高之宝。
《定武兰亭》之所以在南宋特别被尊奉,除了误会比附说成是欧阳询的摹本之外,主因有二:一、黄庭坚在南宋地位很高,黄之谬论,力捧《定武》;二、《定武》原石刻因被金兵劫走迷失,拓本不可再得,南宋人怀念故都的爱国心情,又增加了这一文物的无比价值。
但在北宋,对《兰亭》意见分为两大派,一派是主张取唐代墨摹本,“有锋铩者为近真”,当时最有学识的书家,如苏轼、苏辙兄弟,都不约而同,认为墨摹本比《定武》石刻好得多。惟有一个黄山谷立异,大反众说,不论笔法的“芒角”近真,讲“拓本”的肥瘦,把《定武》捧上九天,这样一来,大家争着翻刻这个《定武》。到南宋末,贾似道倒台,从他家抄出的《定武》翻刻本,竟达八百种之多!,唐摹本,却少人理睬,米芾表彰的“苏家第二本”唐摹墨迹,却确是最近王羲之原笔的一个希世珍品。
对于书法这样十分高级的艺术品,除非个别的非常高明的摹刻手,能约略存真,落到拙劣人之手中,不要说辗转翻刻,一次翻摹也会弄得霄壤悬殊,其糟无比。《定武兰亭》“八百种”翻本的后果只有一个,假躯壳空存,真灵魂大变。问题的严重,又不在于仅仅关系到贾似道这种附庸风雅的古董收藏家,南宋的书风,因此等缘故,简直愈来愈坏,每况愈下,此时,出现了一个“书法中兴者”赵孟兆页
他是一个由宋入元的人,书功极深,见闻也广,但是苦于书识不高,当时仅存的二三古摹本《兰亭》他都有经眼,题跋,却对《定武兰亭》下了极大了功力。
此事证明:到赵时,享名极盛,但书法真的好传统已然断绝,所存的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东西,而赵的“流风余韵”,势力极大,一直到清中叶,纯粹是“赵董”一派垄断书坛。赵是圆熟甜净,董是浅怯凋疏,加上小头锐面。当时从皇帝起,却奉此为“不二法门”。
当代一般人纵使想超越“赵董”,溯本求源,但他们所能找到的古法,也只是“面条儿”式的《阁帖》之类。
这就无外乎出现了后来的“碑派”,专门从北魏时代的石刻字去求范本,立为标准。这本来是无可厚非的好事,可惜碑派也是严重的形而上学派,只是一味的模仿外表的空架子,不去分辨原书手、刻手的优劣高下,笼统尊奉,又不去认真寻求六朝的真笔法源流,也不知“魏碑体”与东晋、隋唐今楷书的发展关系,生硬照搬,排斥晋唐,末流遂成为一种滞钝僵板毫无变化生气的恶俗字体,很难说比帖派的木流好到哪去,也未见书法找到真的出路。
这么一来,看来像是一个细节问题的“芒角”,它的得失在书法史上却造成了多么严重的后果,影响了千百年来的书坛方向,所以说书法应特别重视“芒角”问题,就不为过了。
(22)综合讲讲书法的几个方面
书法艺术家,是高超的建筑师,他运用汉字的结构法,造出千百种美妙的形、态、姿、致。他的建筑材料不是僵死的东西,而是多变的线条笔触,内含着丰富的力的运行的美。各个建筑连成组、群、又有丰富变化的章法布置,这一切表现出中华民族文化的一种造诣、素养、生气、神采和时代的新精神新风格。他所忌的是万字一同,千笔一法,直来直去,平拉滑拖,呆滞板僵,庸俗油滑,缓弱松垮,缭绕堆垛,更忌扭捏作态,拧眉怒目,拉架摆势,浑身犟功,粗野丑怪,造作假相,自以为高。
艺术是“工到自然成”为最正,也最高,不明此理,就会一味用力造作,自我意识太重,于是处处“作态”。此种态,很难有真好真美的态。水到渠成,功力造诣够了,其态是一种自然的流露,而不是造作。
(23)关于其它
学写字通常先学楷,次学行草,楷书是立,行书是走,草书是跑,这是真的,还不会站立,如何能跑得起来。
学楷书是为掌握基本功。楷书一笔不苟,要练这个认真的功夫,也是做事的态度问题,故绝不可忽视。时至今日,用楷书的场合实已不多,反而不如行草更有用处。当然,大草、狂草,不必普遍提倡,因为范本极少,作者主张楷法之后着重学学行书,大为必要。
古人把行草分得很细,按“行”和“草”的程度不同,分成很多的层次,大约有九层,各有不同的名目,俗语则笼统呼为“连笔字”,这个“连笔字”,不要小看它,关系却是不小。
严格的说,只能写真楷书的,还不能成为真正的书家。所以孙过庭提出“作草如真,作真如草”,又说“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写的是草书,却要像真书那样笔笔不苟,处处有起落,有交待,不是任意信笔乱画就叫草书。写的是真书,却要笔法活变,意态飞动,不是“刻板”死字。他甚至认为不通一点行草意法的真书,简直不够书法,因为那样写成的字很可能文字符号性多,而书法艺术性少。
书法离不开字体,字体也受书法影响。会一点行书的,比起不会的来,他的一般书写的流利度、快速度,以至好看的程度,差别之大,有时很是惊人,决不可忽视。汉字的难写,也就靠行草书相对减轻了。会写行草的,笔下流畅,并不觉得汉字繁难,所以作者认为青少年有一些行书的指导和训练,好处很大。
关于选范本,不易讲,有好几层的原因。第一、各人笔姿、笔路不同,不能也不应定出一个死的“方案”来,要人人非依它不可,那又是形而上学了。第二、教给人如何选范本的人,他们的路数、认识、理解,又各自不同,一种“方案”,在此家赞成,在彼家反对,究竟谁是谁非,学书者不能自断,别人也无法代断,谁的看法也难成为定论。第三、范本本身问题又不简单,讲起来十分麻烦。第四,还有帖本是否方便易得的问题,举出名目来,国内目前尚无印本,无法觅购,也等于白说。
“帖派”主要学帖,“碑派”主要学碑,如果你要选范本,先得自己定下来,在“帖”“碑”二派之间,你愿走哪条路。
“帖派”在古代分类法上,是“行狎书”的字体风格,是写在笺纸上的活的字。
“碑派”写出来很有气魄,笔致浑厚高古,架式雄伟,作为大幅中堂,对联,悬在大厅里确有气势,这种书体风格,在古代本叫做“铭石书”,是“高文典册”的永垂不朽的“庙堂体”。
这两种字体是内容、用场迥异不同的字体,前者是我们日常的生活、工作范围以内的书体,后者是专为“摆样子”用的书体。我们有时可以戏称,前者为“纸墨书家”,后者为“金石书家”,前者和文学作品关系密切,后者和公文,史料关系密切,前者写的不够好,还是活的字,后者写的不够好,就是刻板字,很像“墨色的碑”。
讲艺术的事,要知道有过一句名言,说是“可以惊四筵而不能适独坐”。惊四筵,乍见动人心目,再看三看,不过如此。适独坐的,有时却百看不厌,玩索不尽,其味历久弥永。这种分别,也要自我感受。
如果,结合“方便性”来说,可以先试试,写一个短时期汉隶,给楷书笔法奠奠基础,可即用《汉隶书选字帖》,其中前两种《朝侯小子残碑》和《张景碑》尤好,学学很有益处,其他好汉碑如《礼器》等也极好。然后学一两种好唐碑楷书,因目前没有合适的墨迹楷帖出版,可取欧阳询的《皇甫君碑》,笔法姿态最好,《九成宫》不必多学,易落于呆板。已印过的欧书《千字文》,不是原真迹,是钩填本,也可学。学得笔底下有点骨干,可换习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笔法最活,有了这两家楷法的基础,再尽可能地多看或选临唐初其他家的楷法,领悟他们的用笔异同变化。进而可学行书,最方便,可取的,数来数去,还是以《集王圣教序》为合宜,《兴福寺碑》集王字风神尤为流美,也可临习。同时也可参看、参学最有名的唐摹王羲之行书帖,如《何如》、《奉橘》等帖,如能看出它们和《圣教序》的笔法间的关系,就有心得了。日本的《丧乱》、《得示》、《孔侍中》等帖也极好。《快雪时晴》帖作者认为不能代表王的真笔法,学不好很容易成为赵子昂,可不必取法,《兰亭序》极重要,但问题异常复杂,初学很难理解、掌握,应俟学书法有了一定造诣之后,再去研习。还有一种集王羲之书而成的《千字文》墨摹本,笔法极精,但也很不易学,如能得到印本,应留意细看。草书可先学孙过庭《书谱》,也有墨迹影印普及本。但此帖过于随便、草率、颓唐等败笔,对初学者不利。宜善加抉择,学其长处。贺知章《孝经》极好。如《大观帖》亦有新印本,摹刻精好,也可作为墨迹以外的范本。
这只是一个很粗的举例,每一种帖又有它本身的很多知识,需要细细体会。
选择范本,第一要看的就是尽可能选取墨迹本,这是针对书法史上的弊病而采取的。从宋代起,刻板印刷发达起来,古代书籍靠抄写卷子的情况发生了根本变化,有了印版书,
抄写卷子逐渐减少,人们目中所见,多属“刻板字”。极少数书法名迹,成为万金之宝,为少数最“有办法”的人所垄断,纯粹成为古董,因为太宝贵,连收藏书者都舍不得打开,更不用说作为范本临写了,所以学书之人只好求“汇帖”,“汇帖”也极难得,很快被翻得一塌糊涂,只好去学石刻,又回到了“刻板字”的局限之中。这个问题存在了一千多年,总是没有很好的解决办法。
这几十年有了照相印版术,可以与真迹毫发不差,而且化身千亿,这是古代学书者梦想所不能有的大事,我们为何放着这样的好条件不利用,而依然去迷信、死抱“刻板字”。
所谓墨迹,需要说明的是要重视向来为士大夫所轻视的“写经手”的作品,他们大抵世代传业,功夫精纯,笔笔敷畅饱满,精神完足。如敦煌莫高窟内的手写卷子,大多数是唐代的好作品,保存着历代传下来的好笔法。过去士大夫只知迷信名碑帖,其实任何轻视“写经手”的思想、眼光都是很荒唐的。其实这些都是前人所无法得见、也不知宝贝的最直接得真的上等范本。
关于学书是否需要下苦功的问题,原则上不会是反面的回答,不过,我们现在学书与古代士大夫条件大不相同,他们是“池水尽墨”,“日课万字”,我们有很多复杂的工作要做,谁也成不了“专业书家”,因此不可能在写字上花太多的时间。但这一点不是问题所在,我们中国常讲“功夫”二字,最有意味。各种艺业,多讲功夫深浅,功夫就是积少成多,持之有恒,循序渐进,不骄不躁,水到渠成。强扭现造出来的,绝不会有“功夫”,即使有,那也是假的,每天挤出一刻钟到二十分钟,不慌不忙,写多少字算多少字,不存任何急于见功的念头,这样每日必行,坚持为例。隔一个月将你积起来的字迹对比,就会发现进步,这样自己也增加了信心和兴致。
没有什么“奥妙”“秘诀”“窍门”“捷径”,花多少功夫,这点工夫就会给你相应的报酬,绝不会亏负你。当然,也切忌浅尝一下,便沾沾自喜,目中无人起来。书法的艺术境界高处,是需要不断跻攀的。登到一个高度才会看得见更丰富的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