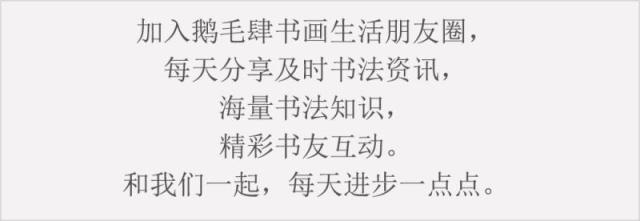唯有书法与爱情,不可辜负
唯独两件事不行,那就是书法与爱情。
爱情,是因为其普遍、
其泛滥和流行,属下里巴人;
书法,却是因其孤傲、
其清寒和不羁,类阳春白雪。
一为入世,一为出世,
前者是人的事,后者是非人的事。
非人即仙,这是对书法最高的评价了。

两者,一个在东一个在西,
一个为马一个为鹿,
但奇怪的是,命运却十分相同。
同在什么地方呢?
说来很简单,那就是两者的所指都很难确定。
什么是真正的爱情呢?
爱情几乎随处可见,
白头偕老的夫妻在这个世界上数不胜数,
可真正的爱情又有多少?
什么是真正的书法呢?
从稚童的描红到大师的临帖,
单从情状看,谁能说有什么不同?
博大精深倾其毕生,是寥寥数笔,
附庸风雅奴颜媚骨,也是寥寥数笔。
谁能辨其真伪?谁敢说谁就是书法?
谁又敢说谁就是真正的书法家?
所以,书法和爱情是不便谈论的,
不是不能谈论,而是无法谈论。
爱情是一头象,谁寻找爱情,
谁就是摸象的瞎子;
书法也是一头象,而且大象无形,
谁谈论书法,谁就是摸象的瞎子的瞎子。

一个人,在路上走,长途跋涉已多年,
很难有凡间的事能让他停下来,
能让他改弦易帜卖身投靠,惟有爱情;
这个爱情,不是概念的爱与情,
而是爱的生理如心跳、惶恐、莫名兴奋与寝食难安,
情的心理如缠绵、沉迷、如胶似漆与相见恨晚。
同理,一个人,从艺多年,
绘画、诗文、琴与瑟、理学与玄学,
均狂放不羁,
很难有某一单项的艺术能让他跪伏称臣,
能让他顷刻闭嘴噤若寒蝉的,惟有书法;
这个书法,也不是概念的书与法,
而是“书”的尺度如狂放、抑制、
一泻千里与咫尺腾挪;
与“法”的范畴如造纸、制墨、研磨、腕力、笔触
以及墨纸的结合和下笔的不稳定性。

书法,写的是字,
但,书法是不把字当字写的,
既然不把字当字写,为何写的又却是字?
这是书法的绝妙之处,
但也是书法的无可奈何之处,
是通常所说的破绽,是属于天机泄漏、天衣有缝的。
书法像鱼目,又是珠,乃至于鱼目混珠:
书法写的是字,
所以看书法时有人定要看出字意来。
书法的水,又多是写书法的人自己弄浑的,
什么气功书法、双笔书法的便是。
不过,这些都是小家的事,
大师全不理会这些,大师写的字不是给人看的,
即使两个大师是挚友,也全不看彼此的字。
写字只是一种需要,跟吃饭一样,
有什么好看的。
谁曾为吃饭的样子著过书立过说?
从古到今,看来没有。
大师的字,你当字看,他皆大欢喜;
你不当字看,他也皆大欢喜;
哪怕你不看他的字乃至骂他的字,他也皆大欢喜。
不过,这样的大师,从古至今又有几人?
二王?四僧?反正,我不知道!

所以,还是回过头来谈浅薄的爱情。
爱情不是书法,不是可有可无的,
爱情是人一生中必须进行的一件事。
你可以说我不喜欢书法,
但你不可以说我不要爱情。
爱情也很可以鱼目混珠,
比起书法而且要更容易一些,
书法毕竟还要写,还要研墨,
还要一支叫狼毫的笔。
假的爱情只需甜言蜜语,只要有钱,
只需有一副好身胚。
其中,钱稍稍难些,其他都是现成的,
用不着去别处张罗。
婚姻可以买卖,爱情却断断不能作金钱交易,
一交易便不再是爱情了。
书法,起码也如同这爱情,不能买卖,
那些以尺论价的书法家,想必是知道这些的,
不过,他们不把自己当大师看,你也拿他没办法。
有爱的人,见花非花,见人非人,
见独木桥犹如见康庄大道;
有情的人,负重若轻,蒙难若易,见飞泪若见微笑。
反过来,知书之恢恢乎如横空出世的人,
见墨不是墨,见芍药不是芍药,
见命悬一线犹若见拈花一笑;
而,知书之不外乎写写字画画图的人,
见砚也不是砚,见芭蕉更不是芭蕉,
见宽衣解带的女子一如见失散多年的姐妹。

知爱情与知艺术疆界的人,
是无福无缘无现世作用的人,
却又是星空之宿物;
爱情的一见钟情与艺术的油然而生,
它们,才是同一个东西,
一个命悬一线,一个拈花一笑。
将书法与爱情放在一起谈,
似乎有些低级趣味,但细想想,
哪样东西和书法放在一起谈,不低级趣味?
书法不好谈,谈的又可以是书法,
仅这两桩,便可见书法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