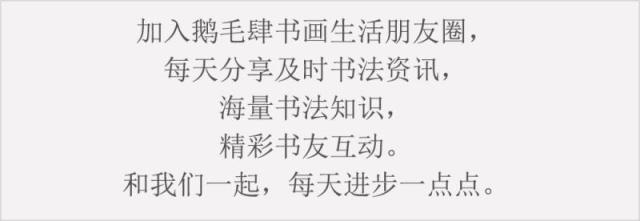书法菩提·夷门民国书法人物

书法菩提·夷门民国书法人物
■张晓林
邹少和
邹廷銮(1872—1945),字少和,书法师承晋唐。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秋,邹少和在开封的河南贡院参加乡试,考中第389名举人。第二年,参加礼部会试的时候,运气却没有那么好,名落孙山。
他父亲托门子,掏了些银两,在京城巡警部给他捐了个“警正”的职位。邹少和对这个“警正”不感兴趣,很是苦闷。那些日子里,他痴迷上了戏曲。很快,他与杨月楼、汪桂芬、俞菊生等京剧名角都成了好朋友。
辛亥革命爆发,邹少和告别京城戏曲界的朋友,回到开封,在经教胡同定居下来。他与萧劳、张伯驹、靳志成立了夷门书画社,探讨绘画和书法。
邹少和的书法四体皆工,尤以行草见长。他的行草独辟蹊径,以苏轼笔意写晋人风韵,萧散而蕴藉。他认为,书法得给人以美感,如果书法去执意追求丑的东西,那不知书法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
然而,书法对邹少和来说,只能算是客串,闲来捻管罢了。
人们津津乐道的还是他的画。在开封,他画画的名气,要比他书法的名气大得多。
他是个花鸟画家。他的花鸟,走的是北宋徐熙一路,野逸萧散,山林之气浓郁,没有一点文人的造作。他并非不会画山水,在京师的时候,他的山水画照样技压群雄,田际云、程砚秋、尚小云等很多戏曲界名伶都跟他学过画。京剧大家姜妙香跟他学画时间最长,后来又推荐弟子沈曼华来跟着学。
回开封后,邹少和不再画山水画,完全是因为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祝鸿元。祝原在省政府任职,雅爱丹青,专注于山水画。晚年隐居夷门,以卖画为生。经人介绍,豫西大实业家耿某曾来开封京古斋买祝鸿元的山水画,一进店门,他却被另一幅山水画中堂吸引住了。那幅画画得烟雨空蒙,层峦叠嶂,气势壮阔。然而,山深处勾一茅舍,有二高士煮茶论道,给画面平添了几许婉约。整幅画意境幽邃脱俗,耿某看得两手竟攥出汗来。耿某阅画极多,能让他一见心动的不多。
后来,耿某没有买祝鸿元的画,却把邹少和的那幅山水买走了。邹少和听说了这件事,跌足长叹,以后就洗手不再画山水画。
邹少和生性耿介,偌大的开封城,他愿意交往的人不多。但他能与祝鸿元作彻夜长谈而不知疲倦,便把祝引为知己了。从北京回到开封,生活里少了京剧、梆子戏,邹少和觉得丢了魂一般。祝鸿元劝他去看看豫剧祥符调,并且对他说:“祥符调中有个叫陈素真的,唱《三上轿》,那才叫好!”
邹少和说:“不看!”
邹少和有个多年的怪毛病,从不看坤角的戏。他也说不出什么原因,就是讨厌坤角戏。祝鸿元也没说什么,只是笑了笑。
隔几天,祝鸿元备了家宴,请邹少和去小酌两杯。去时,见祝家有一年轻女子,往日未曾谋过面。女子眉目清秀,看上去很瘦弱。正疑惑间,那女子向他开口打招呼:“您老来啦?”一霎间,邹少和愣住了。这声音宛若雏凤在默林中鸣啼,他还从没有听到过这么美妙的声音,他开始对这个瘦弱的小女子充满好奇。
席间,经祝鸿元介绍,邹少和才知道,和自己打招呼的那个女子就是豫剧名伶陈素真。
接下来的日子,邹少和一口气看了陈素真主演的《凌云志》《齿痕记》《涤耻血》等剧目,越看越想看,只要是陈素真出场的戏,他像着了魔一般,出出都去看,他完全被陈素真的戏给迷住了。
邹少和开始研究豫剧,不久,他写出《豫剧考略》一书,成为第一部研究豫剧的专著。在这部著述里,给了陈素真很高的评价,称她为豫剧中的梅兰芳。
1936年春,京剧名家尚小云来到开封演出,闲暇时去经教胡同拜访他,他向尚小云推荐了陈素真的祥符调。尚小云提出看陈素真的《涤耻血》,在唱这场戏的时候,陈素真的嗓子“倒”了,一时之间,竟无法登台唱戏了,她感到很痛苦。
邹少和常派人接陈素真到家里来,教她画花鸟,画草虫。过一阵子,夏天到了,有人拿了扇面让她画。画好了,看看,不成个样子。邹少和站在一旁,拿起画笔,左一涂,右一抹,再看,像一幅画了。
邹少和专门给陈素真写了一出《蟠桃会》。看了本子,陈素真很喜欢,她在心里说:“我要演火它!”刚演了两场,“卢沟桥事件”爆发,陈素真开始演《伉俪箭》《克敌荣归》等御敌救国一类的武戏。
日本侵入开封,邹少和所在的汴京面粉公司倒闭,他失业了。有旧时好友王某要拉他出来给日本人干事,被他大骂一通赶出家门。
日本投降的那年秋天,邹少和病逝。
邵次公
邵瑞彭(1887—1937),字次公,书法得褚遂良三昧。
黄昏,邵瑞彭次公喜欢去鱼市口街拐角处的“恍惚”茶馆喝茶。这家茶馆养了一只肥硕的猫,通体黑色,两眼黄得像金子一样令人心醉。每次见邵次公进来,它都要跑过去卧在他的脚下,然后,用金黄色的眼睛盯着他看,次公就有了抚摸它的欲望,黑色的皮毛犹如绸缎一般光滑,抚摸着它,次公心底就有颤栗飘过。
要上一壶茶,斟满茶瓯,刚送到嘴边,就听背后有人在咬着耳朵嘀咕:
“听说了吗?河大一个邵姓教授,不仅是杆烟枪,还是个色鬼!”
“是啊!还和他的女学生搞在了一起!”
邵瑞彭坐不住了,他没有回过头去看那两个人的面孔,只轻轻站起身,走出了“恍惚”茶馆。
深秋的开封街头,风竟然凉得刺骨。邵瑞彭裹了裹单薄的衣衫,朝火神庙街的公寓走去。来开封的这些年里,他觉得自己精神的橐囊,正一点一点地干瘪下去。
他怀念起一个人来。
早些年,次公是个天下闻名的斗士。那时候,他还在京城,头上顶着一顶众议院参议员的桂冠,1923年深秋,曹锟贿选总统,他第一个站出来揭发了这场丑闻。曹锟的部下威胁他说:“花钱买选票,总比拿枪顶着你的脑袋让你投票强吧!”次公愤怒了,把曹锟贿选给他的五千银元支票拍照后寄给京沪各大报纸,把贿选事件搅了个满城风雨。
京城待不下去了。为躲避追杀,他先后到过上海和淳安。淳安是他的家乡,在那里,他受到热烈欢迎。石硖师范的学生高举“揭发五千贿选,先生万里归来”的巨大横幅,集体到车站欢迎他。曹锟倒台后,1925年的夏天,邵瑞彭又回到了北京。北洋政府任命他为教育总长,他坚辞不就,从内心深处不愿再涉足政界。在京期间,先是与友人组建“聊园词社”,相互唱和,后又入几所京师大学任教。之所以屡屡变换学校,是因为曹锟的旧属不想放过他,对他实施了多次暗杀。
这个时候,河南大学校长许心武替他解了暗杀之围。1931年暮春,许校长聘邵瑞彭出任河南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许校长对他很厚爱,每月给他的薪酬是300大洋,是河南大学所有教授中薪水最高的。邵瑞彭有吸大烟的癖好,住在学校不方便,许校长就在财神庙街给他租下一处宅院。这处宅院有九间房子,三间作为客厅,三间作为书房和卧室,此外的三间当作厨房和厨师住的地方。来开封时,次公想带家眷一同前往,他老婆不愿意。她说:“我不去那个遍地牛二的地方!”
来开封不长时间,许心武就调离了河南大学。尽管相处的时日不多,但每到心绪有了波动的时候,邵瑞彭都会奇怪地想起他来。
为排遣漫长秋夜的孤独,次公与卢前、武福鼐、朱守一等人组织了金梁吟社,有一批酷爱诗词的河大学生和社会才俊参加了进来。他还自筹资金,帮学生出了诗词合集《夷门乐府》,几乎是同时,他的词集《山禽余响》问世,好评如潮。施蜇存专门给他写来了一封信,称他的词:“宗《花间》、北宋,出入清真、白石,甚或过之。”
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很喜爱次公的词,把他称为“小柳永”,《山禽余响》里的词,闲来还能背出几首。一个时期,次公成了刘主席的座上宾。
河南省图书馆想刊印一套本省先贤的著作,临下印馆了,才发现经费差了一大截。馆长井俊起找到了次公,想让他去刘峙那里疏通疏通。次公笑着说:“份内之事,当尽力!”隔一天,次公拜访刘峙,说起出书的事,刘峙当场就安排属下给办妥了。
刘峙政务之余,也时不时作几首小诗,时间一长,也有100多首了,他想刊印成册,找人作跋,就找到了邵次公。跋成,竟终篇不题刘诗一字,云里雾里,让人看得糊涂。武福鼐一次问起这件事,次公说:“刘某之诗,真不知道该怎么去说。”一个时期,河南颁布戒鸦片令,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告示。次公不予理睬,他吸食鸦片,却不会烧烟泡,常烧伤鼻子,因此他的鼻头总是黑黑的。他黑着鼻头去见刘峙,有人看不过去,提醒刘峙说:“攸关政令!”刘峙就慢慢疏远了次公。
1935年初,靳志回开封定居。次公与靳志在北京时同为寒山社成员,属于旧时相识。两个人重聚开封,自是来往密切,一有闲暇,便相邀小酌。他们二人还有个共同的兴趣,就是书法。次公的书法原来走的是欧阳询一路,这时忽然对宋徽宗的瘦金体入了魔,每日临《赵佶千字文》数十纸。靳志看着老友的背影,暗自叹道:“次公恐怕将有桃花之劫!”
竟果然被靳志言中。
金梁吟社里,有个叫李澄波的女诗人,在尚志女校教国文。本来已经结婚了,她不顾丈夫的反对,硬加入到社里来。她喜欢读次公的词,读《山禽余响》,都读出相思来了。每次雅聚,她的目光只追随着邵次公一人游走。那目光柔得像三月的桃花,满坡粉红色的诱惑。次公读懂了这目光,可他选择了沉默。
冬天的一个夜晚,李澄波只身一人到财神庙街23号,找邵次公请教诗词创作上的问题。坐下不久,窗外就下起了漫天大雪,继而狂风大作,狂风搅着鹅毛般的雪片,把窗纸敲打得“噗噗”直响。这一夜,李澄波没有走。第二天,李澄波羞涩地说:“这是天作之合。”
很快,他们的事情东窗事发,李澄波的丈夫一路破口大骂,旋风似地闯进河大校园。那时候,次公刚刚下课走出教室,一群学生簇拥着他,他说了句什么风趣的话,学生们便清澈地笑起来。李澄波的丈夫就是这个时候走向前去的,他一把扭住了次公的衣领,当着众人的面狠狠扇了他两耳光!
耳光事件后,次公的烟瘾更大,鼻头更黑了。一些旧友同事,都用异样的眼光看他,对他冷淡了许多,交往也日渐稀少。尤其让他伤心的是,他的得意门生武福鼐也不再登他的家门。金梁吟社也风吹雨打散了。有一天,他路过武福鼐家门口,这天他阴郁的心情稍稍透出一丝阳光,他走进院去。武福鼐的妻子正在院里喂鸡,见他进来,掂起笤帚疙瘩对着一只老公鸡骂起来:“你个好打野食的东西!”
次公默默地退出院门。先前,这个贤惠的女人每次听说他来,都是早早熬好了燕窝粥等着他。武福鼐知道,在北京中国学院教书时,邵次公最喜欢喝的就是燕窝粥了。
李澄波和丈夫离了婚,和次公住在了一起。说等选个好日子,把结婚仪式给举行了,次公木然地点点头。日子一天一天过去,次公的心情也一天一天地坏下去。
又是一个漫天大雪的冬夜,李澄波外出参加了一个诗会。这天夜里,邵次公吞鸦片自杀了。
李澄波彻夜未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