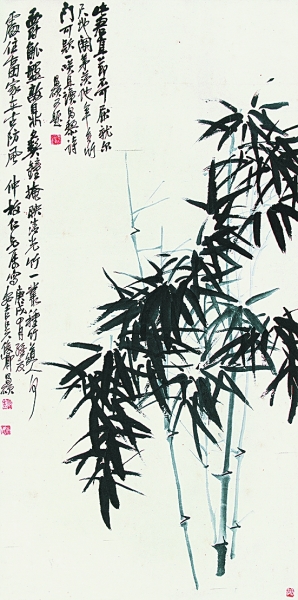吴昌硕鉴定-石鼓体书法欣赏
清代中叶以后,出土了大量的汉魏碑志,为书法界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碑学大盛的渐变风潮打破了帖学一统天下的传统局面,一些书法家大力倡导碑学,使碑学一跃而占据较高地位,其间《石鼓文》成为较热门的范本,邓石如、张惠言、杨沂孙、吴大澂、阮元等极力推崇,潜心临仿之。社会上要求书法变革的呼声也渐趋强烈,有人大胆地试以新的创造,走新的路。如邓石如,打破了自秦以来过于呆板工整的作篆方法,采用隶书笔法来写篆书,而伊秉绶则改变了以往隶书的传统写法,以篆书笔法写隶书,杨沂孙、吴让之等均在作篆笔法上融进了新意,创出了自己的书风。纵观中国书法史,清代的篆书达到了兴盛时期,不论从实用性或是赏玩性,还是从艺术的追求上都超过了以往各个朝代。这一切现象,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吴昌硕的书法艺术。
吴昌硕由于家庭的熏陶,早年就悉于书法篆刻,颇受邓石如、杨沂孙、杨岘等的影响。而从吴昌硕早期所临《石鼓文》看,则受阮元本《石鼓文》的影响颇多。阮元本是经过阮元对《石鼓文》的整理,推究字体,摹似书意,由张燕昌双钩摹写,海盐吴厚生刻凿后的拓本,与唐拓本有较大的差异。笔者据有关资料考查,结合吴昌硕早期所书《石豉文》作品与阮元《石鼓文》拓本,对照唐拓精本《石鼓文》进行分析比鉴,吴昌硕早期临的《石鼓文》均出自阮拓本。从用笔来看,唐拓本《石鼓文》精细均等,起收裹藏,起笔、行笔、收笔呆板而无变化,而阮元本则有了较大较多的粗细变化,起笔有大圆头、圆头、尖头等;行笔有中间粗两头细、中间细两头粗,前粗后细,前细后粗,粗细相等等;收笔有剑尾、圆尾、尖尾等。线条变化丰富,有较多不同的运笔方法,而吴昌硕正是通过对阮元本的临习得到了从别的碑帖中所得不到的东西,也就是说,吴昌硕篆书变幻莫测的线条或多或少得益于阮元本。我们从看,阮元本《石鼓文》与唐拓本《石鼓文》的结体之间比较,有许多明显的不同之处,如“车”、“蜀”、“?”、“鹿”、“麀”,出现了上下舒展、左右略紧,以及参差大小等一些结构变化,吴昌硕早期临作的结体,颇似阮元本而非唐拓本,这也为吴昌硕篆书的创立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这样说,吴昌硕如果没有阮元本的初临阶段的话,那他的篆书将又是另一番风味了。
下面通过吴昌硕早期至晚期的各年龄段所临或创作的篆书代表作品,探析他所走过的轨迹。

33岁临《石鼓文》横幅
由于吴昌硕早年即学篆刻,因而对学篆也成了他的爱好之一,广泛收集籀篆汉瓦碑刻,孜孜以求,日夜苦练,此前求得阮氏拓本《石鼓文》,从此开始了吴昌硕不拘一格的篆书生涯。此幅作品从用笔上看,虽然觉得有些稚嫩,但基本符合《石鼓文》的书写要求。起笔时谨慎藏头,多呈圆头,中部运笔力求中锋,线条略有粗细变化,收笔时小心裹尾;结体较接近阮拓本《石鼓文》,如:“速”、“求”、“车”等,整幅字工稳平整,形态对称而和谐,默色浓润而厚重。

61岁临《石鼓文》四行
可以说吴昌硕在45岁以前所临《石鼓文》较为规整,中锋运笔,精心结体,而四十六七岁至60岁这段时间是吴昌硕篆书初显面貌阶段,至60岁以后“确立自我面目”(沙孟海论《吴昌硕先生的书法》)。此时在《石鼓文》的临习和创作上,他独具慧眼和胆识,倾注了全部的心力,遍集宋明佳拓,再参与秦权量、琅琊台石刻、泰山石刻和雄悍浑厚的西周金文,旁通秦玺、汉印、瓦当,融进自己独特的个性风格,进行大胆变革,一发而不可收,初创出崭新的吴派书风。从这幅作品中可以看出,由于线条的分合聚散,快慢粗细,墨色的枯润变化,均显示出深刻的韵律和苍劲朴茂的意趣;结体气势开张,不似《石鼓》胜似《石鼓》。能把平整圆匀的《石鼓文》写得如此具有个性,在篆书史上很难找到这样一种典型:古得高雅出奇,又新得前无古人。
62岁临《庚罴卣铭》大轴吴昌硕所书金文虽然不多,然而却显现出敏捷的观察力、深刻的理解力、准确的把握力,以及超前而独特的审美观,他的金文作品开宗立派,基本跨越了时空的限制,向后世展现出篆书艺术新的审美模式。从这幅金文作品中我们看到,圆润、流动的线条在他的笔下却呈现出刚柔相兼、斑驳自然、凝重古雅的独特美感。在用笔上不拘中锋,时以侧锋、露锋取势,藏露分明,方圆兼备,粗细明显,间以飞白,笔画结体相同之处,均求异,如“王”、“用”、“宝”、“庚’等字,或长或短,或曲或直,起笔收笔多方出锋;结体上,采取斜正、大小、长短、参差、错综的方法,追求一种寓险于平、寓动于静的意境,使每个字各显其势,姿态多变,大气磅礴;墨色的浓淡枯湿而带来整体效果的错落分布,均衡有致。值得一提的是,虽是所临金文,但我们从他的用笔、结体中仍可以看出吴昌硕对《石鼓文》笔法的参用,字里行间无不浸透着《石鼓文》的韵味。
67岁篆书《修震泽许塘记》《修震泽许塘记》是吴昌硕中期的得意之作。他以《石鼓文》笔法入篆,信手而成。纵横的点线中,每一笔都精意,因为运笔速度的疾徐,使得线条轻重粗细互见,笔务豪肆且酣畅,颇有节律感,如“泽”、“水”等字,起笔多裹藏圆转,收笔不刻意回锋,或截笔而提,或顺势出锋,或圆转回锋;结字已显恣肆,中宫收紧,字的上下左右以自然参差取势;同时墨色变化较丰富。
70岁集《石鼓文》八言对联,这是吴昌硕晚期的作品,也是吴派书风成熟期的开始。“书之所贵贵存我,若风遇箫鱼脱筌”(《缶庐别存》),正是他此时艺术思想的写照。从总体感觉上,字里行间气充力足,纵逸放达,颇显沉雄端庄。用笔圆劲、饱满,婉通而有力度,峻利而取涩势,力能扛鼎但不狂放,线条厚重但不滞浊。吴昌硕在晚年曾说过:“临《石鼓》宜重严而不滞,宜虚宕而不弱。”这也是他浸淫《石鼓》数十年所得出的最宝贵的经验之谈。结体左右紧束,上下纵展。浓重的墨色更显字的雄浑高古、上下左右的疏密关系使字产生强烈的黑白对比效果,增强了空间的跳跃呼应关系。这种种变化,并非是吴昌硕竭尽全力去完成的,而是随意挥写,并不费力的事。这些无不体现出吴昌硕对其用笔的熟谙。

75岁集《石鼓文》七言对联
此作是吴昌硕晚期作品中的得意之作,此时也是创作的鼎盛阶段,沙孟海评价基作品“恣肆烂漫,独步一时”,出神入化,炉火纯青,达到了郁勃纵横、古茂雄秀的境界。在用笔上以粗细不同的笔触来表现丰富的线条,起收及转折处;方、析、圆并施,化方折为圆转,寓方于圆,方中寓圆,多面出锋;结体上,左右高低更参差险劲,内外疏密更富于变化,上下大小更强调形态,点画少的字,结体紧密,如“子”、“平”等,点画多的字,开张舒朗豪迈,如“原”、“处”、“贤”等字。我们从中更可以看出其内在的特点:彻底改变了《石鼓文》略显方正和圆匀平整的形态,充分显示出极旺盛的艺术生命力。
此作是吴昌硕晚期末的作品。观赏这幅作品,可结合对照他于60至80岁所书作品,我们会惊奇地发现一些不同的变化,即有些返归平正了。正如唐代著名书论家孙过庭论学书时说:“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孙过庭《书谱》)而这后一个平正,便理超悟之后的升华,这不仅要有前两个阶段的深厚功力,而且还必须有博采兼收的全面修养和独特的领悟。我们从整幅作品看,用笔沉厚平缓,结体雅和凝重,稍有斜侧呼应、大小长短,显得沉雄古朴、苍辣深沉、逸气内蓄。吴昌硕曾于65岁临《石鼓文》末自题道:“予学篆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于是,我们在其最终风格中看到了平中寓奇,奇中寓平的高远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