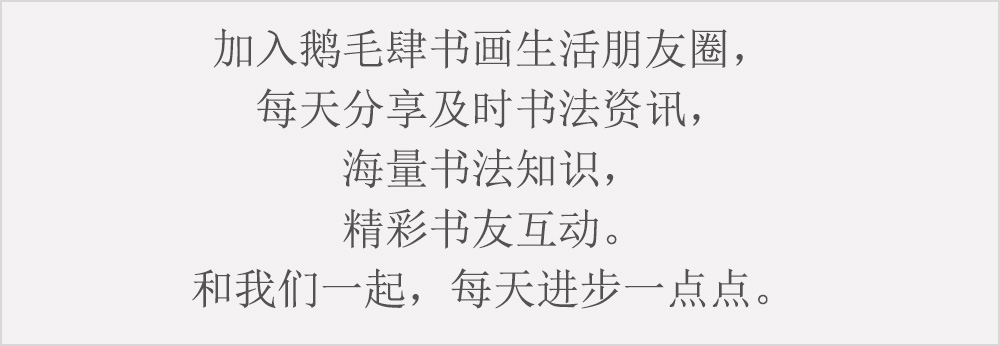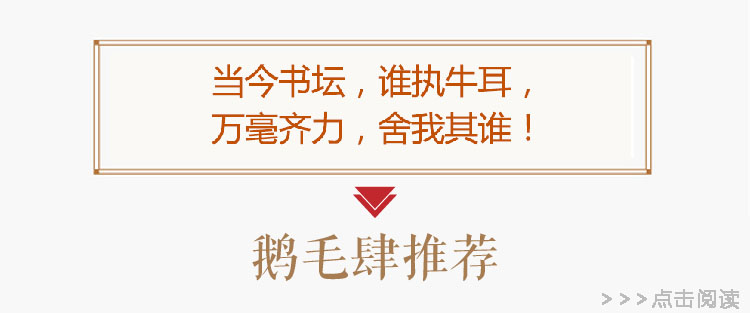瓷片是文明的碎片
2017-09-01 15:54:19 来源: 点击:
沈嘉禄
作为上海古玩收藏界的资深人士,沈胜利携学生刘国斌、其子沈恺宇策划并编撰《谈瓷侃片——中国历代名窑瓷片鉴赏》一书于日前面世。书中作为标本解读的历代瓷片都是他们悉心收藏的。他们从数十年来捡拾、购买、交流而来的一千多枚瓷片中遴选出三百多枚,力求做到每一枚都有不可替代的标本价值。
(一)
在中国古代,匠人地位低下,居于社会上层的文人对“劳力者”的生产实践又比较轻视,所以古籍中对瓷器、玉器、木器、铜器、金银器、织绣等生产工艺的记载极为稀少。明清之前,匠人姓氏和制作年代出现在工艺品上的情况极为罕见,这为今人考证器物的产生年代与社会背景,布设了许多盲点与难点。但是,文物环境提供的信息还能为我们提供管窥蠡测的路径。比如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认为在宋代与明代之间,应该有蓝底白花的瓷器存在,尤其是冯先铭先生已经试探性地提出元代青花瓷的概念,但事实上,许多人还是将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当作明代永宣时期所出的粗陋产品。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约翰·波普通过对英国、伊朗、土耳其等国博物馆所藏数十件青花瓷器的考察,撰写了《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中国瓷器》一书,尤其是他还以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写有“元至正十一年”纪年题记的象耳大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让国内专家有如梦初醒、醍醐灌顶之感。
 元青花的概念让中国专家脑洞大开,那么它就是中国青花瓷的肇始?倒也未必,1957年和1970年,考古专家先后在浙江龙泉和绍兴两座宋塔塔基下的夯土层里出土了一共十几枚青花瓷碎片,有人据此提出了青花瓷始烧于宋代的说法。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又有人在扬州唐城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枚绘有几何图案的青花瓷片,这块瓷片为研究我国青花瓷起源开启了新思路。多年之后,在扬州旧唐城遗址范围内再次出土了十多枚青花瓷片,关于青花瓷始烧于唐代的说法就有了更加有力的证明。
元青花的概念让中国专家脑洞大开,那么它就是中国青花瓷的肇始?倒也未必,1957年和1970年,考古专家先后在浙江龙泉和绍兴两座宋塔塔基下的夯土层里出土了一共十几枚青花瓷碎片,有人据此提出了青花瓷始烧于宋代的说法。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又有人在扬州唐城建筑工地上发现了一枚绘有几何图案的青花瓷片,这块瓷片为研究我国青花瓷起源开启了新思路。多年之后,在扬州旧唐城遗址范围内再次出土了十多枚青花瓷片,关于青花瓷始烧于唐代的说法就有了更加有力的证明。
十几枚瓷片,将中国青花瓷烧造的年代向前推进了九百年。小小瓷片就像一根扛杆,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坚实支点,撬动了中国陶瓷史、中国美术史以及中国外贸史。
故宫博物院专家冯先铭先生曾经透露,在境外有三件完整的唐代青花瓷器,一件为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条形纹三足鬴,一件是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花卉碗,一件是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后来我从多种考古书籍中得知,在伊拉克撒马拉地区曾有类似的唐青花瓷片出土,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内。过了数年冯先生又透露,在海外又“发现”了两件唐代的青花瓷器,一件是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花卉纹碗,另一件是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
 那么这些被掩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唐青花,是不是产于景德镇的呢?文物专家又告诉我们:目前出土的唐代青花瓷,应该出自北方窑口,大多具有巩县窑的特征。而景德镇成规模烧造青花瓷,应该是从元代至元十五年设置浮梁瓷局以后开始的。虽然在1978年杭州出土的八件烧造于元代至元十三年的青花瓷器中已经看到了元青花横空出世的曙光,但青花的“着墨”尚处于“点缀”阶段,远远达不到“描绘”的程度。
那么这些被掩没在历史长河中的唐青花,是不是产于景德镇的呢?文物专家又告诉我们:目前出土的唐代青花瓷,应该出自北方窑口,大多具有巩县窑的特征。而景德镇成规模烧造青花瓷,应该是从元代至元十五年设置浮梁瓷局以后开始的。虽然在1978年杭州出土的八件烧造于元代至元十三年的青花瓷器中已经看到了元青花横空出世的曙光,但青花的“着墨”尚处于“点缀”阶段,远远达不到“描绘”的程度。
(二)
沈胜利先生精通玉器、瓷器、字画以及杂件鉴定。他19岁就进入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在组织安排下拜孙经品先生为师。孙经品先生确立师徒关系后即送了一枚瓷片作为见面礼,这是一枚杭州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瓷片,赏心悦目,釉色莹润,釉层肥厚,胎骨为烟极薄。沈老一直保存到今天,也曾让我观赏触摸过。孙经品先生早在民时期就研究瓷片标本,实在了不起。
 十年动乱时期,工艺品进口公司的业务受到极大干扰,老一代业务骨干悉数被打入冷宫,沈胜利就被推到第一线,从公司库存和抄家物资中挑选可供出口的古玩,还要定期去四省一市(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和上海)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和民间征集劫后余存的古玩,经过遴选后一一估价,打上火漆印送至广交会等渠道出口创汇。
十年动乱时期,工艺品进口公司的业务受到极大干扰,老一代业务骨干悉数被打入冷宫,沈胜利就被推到第一线,从公司库存和抄家物资中挑选可供出口的古玩,还要定期去四省一市(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和上海)的古玩店、文物商店和民间征集劫后余存的古玩,经过遴选后一一估价,打上火漆印送至广交会等渠道出口创汇。
 1977年,沈胜利在百废待理的氛围中去扬州征集古玩。扬州市珠宝文物商店得知沈胜利“驾到”,就特意请他鉴定一件“吃不太准”的蓝釉梅瓶。1976年江苏溧阳地震后,扬州有许多市民只得住在临时搭建的抗震棚里,有一位姓朱市民将一件祖传梅瓶送到扬州市珠宝文物商店出售。商店初步判断此瓶为清代雍正年间遗物,随手放在店内待沽。沈胜利与此瓶一照面后当即两眼发亮:梅瓶高43.5厘米,腹径25厘米,溜肩鼓腹,线条流畅,蓝釉白龙对比强烈,白龙刻划细腻,蓝釉发色鲜亮,龙首威猛精进,龙爪孔武有力,火珠周边镶有光焰,整幅图案气韵生动,大有云海翻腾,蛟龙欲升之动态美感。根据种种特征,沈胜利判定梅瓶应为元代遗珍。而且他也没有以买方市场代表居高临下地将此瓶纳入行囊,而是提请扬州同行妥善保管,不要出售。
1977年,沈胜利在百废待理的氛围中去扬州征集古玩。扬州市珠宝文物商店得知沈胜利“驾到”,就特意请他鉴定一件“吃不太准”的蓝釉梅瓶。1976年江苏溧阳地震后,扬州有许多市民只得住在临时搭建的抗震棚里,有一位姓朱市民将一件祖传梅瓶送到扬州市珠宝文物商店出售。商店初步判断此瓶为清代雍正年间遗物,随手放在店内待沽。沈胜利与此瓶一照面后当即两眼发亮:梅瓶高43.5厘米,腹径25厘米,溜肩鼓腹,线条流畅,蓝釉白龙对比强烈,白龙刻划细腻,蓝釉发色鲜亮,龙首威猛精进,龙爪孔武有力,火珠周边镶有光焰,整幅图案气韵生动,大有云海翻腾,蛟龙欲升之动态美感。根据种种特征,沈胜利判定梅瓶应为元代遗珍。而且他也没有以买方市场代表居高临下地将此瓶纳入行囊,而是提请扬州同行妥善保管,不要出售。
扬州同行喜出望外,后来还特意请南京博物院王志敏教授再行鉴定,认为沈胜利的结论完全正确,此物确系元代江西景德镇窑烧造的蓝釉龙纹梅瓶,国宝重器,世所罕见。现在,这件稀世珍宝陈列在扬州博物馆内,馆方为镇馆之宝设置了一个专厅,我几年前还特地去礼瞻一番。
 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存世只有三件,一件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一件在北京颐和园管理处,这二件高只有24厘米,且有损伤。
元代蓝釉白龙纹梅瓶存世只有三件,一件在法国吉美博物馆,一件在北京颐和园管理处,这二件高只有24厘米,且有损伤。
沈胜利一言定乾坤的那年,才36岁。未及不惑之年的沈胜利何以在元代蓝釉白龙梅瓶面前不疑不惑呢?这与他多年来一直通过寻访、收集、分析瓷片来进行古陶瓷研究有关。当年孙经品先生馈赠他一枚富有象征意义的杭州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瓷片,等于给了他一把打开陶瓷文化宝库的密钥,后来沈胜利还经常请教苏州市文物商店专家张永昌先生和王志敏先生,两位都谆谆嘱咐他以田野考古方式收集瓷片,以拓展自己的眼界。从此他经常在赴外省市公干之余,在古运河、古码头、建筑工地等处捡拾瓷片,这些瓷片都成了他在上海文物商店当经理助理时辅导年轻人的标本,自己一片也没留。直到沈老退休后,才开始丰富自己的积累,寒来暑往,经年累月,也有近千枚珍贵瓷片入藏鉴古精舍。
 这次,他携学生刘国斌、公子沈恺宇策划并编撰《谈瓷侃片——中国历代名窑瓷片鉴赏》一书,书中作为标本解读的历代瓷片都是他与学生、公子悉心收藏的。他们从数十年来捡拾、购买、交流而来的一千多枚瓷片中遴选出三百多枚,力求做到每一枚都有不可替代的标本价值。
这次,他携学生刘国斌、公子沈恺宇策划并编撰《谈瓷侃片——中国历代名窑瓷片鉴赏》一书,书中作为标本解读的历代瓷片都是他与学生、公子悉心收藏的。他们从数十年来捡拾、购买、交流而来的一千多枚瓷片中遴选出三百多枚,力求做到每一枚都有不可替代的标本价值。
 国斌兄早年跻身收藏领域,功勋卓著,自幼羲之临池,怀素书蕉,入列蒋凤仪先生门墙,隶书一门颇得礼器、史晨之风采神韵,后拜张森先生为师,受乃师悉心指授,更有迎风标举之丰美仪。他以书画与漆器收藏怡养性情,略窥门径,转而兼攻陶瓷收藏,成为沈老嫡传弟子,鉴赏水平与日俱进。沈公子恺宇兄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对古陶瓷怀有浓厚兴趣,加之严父耳提面名,思路开阔,触类旁通,进步神速。得闲时恺宇兄也趋步追随乃父辗转于荒郊野地、市肆冷摊,采集瓷片不余遗力,目光独到,解读瓷片工艺特征,一点即通,时有真知灼见让乃父与国斌兄又惊又喜。
国斌兄早年跻身收藏领域,功勋卓著,自幼羲之临池,怀素书蕉,入列蒋凤仪先生门墙,隶书一门颇得礼器、史晨之风采神韵,后拜张森先生为师,受乃师悉心指授,更有迎风标举之丰美仪。他以书画与漆器收藏怡养性情,略窥门径,转而兼攻陶瓷收藏,成为沈老嫡传弟子,鉴赏水平与日俱进。沈公子恺宇兄幼承庭训,耳濡目染,对古陶瓷怀有浓厚兴趣,加之严父耳提面名,思路开阔,触类旁通,进步神速。得闲时恺宇兄也趋步追随乃父辗转于荒郊野地、市肆冷摊,采集瓷片不余遗力,目光独到,解读瓷片工艺特征,一点即通,时有真知灼见让乃父与国斌兄又惊又喜。
(三)
今天,我们可以从《谈瓷侃片》这本书中获得什么呢?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沈胜利从事古玩行业超过半个世纪,视野开阔,经验丰富,沈老的许多鉴赏知识,在具体到样本分析时,更显出老辣而精妙,通过细微之处比照后的解读,也容易让人铭记。而这些知识与秘诀,往往是从成千上万枚瓷片精炼而来的。
 陶瓷的年代确定是一道难题,但是通过书中多枚元青花瓷片上“元至正元年三月初三”、“元至正四年”、“至正八年岁次”、“元至正十年岁次五月初五王备”等题款,再与瓷片的胎骨釉子、旋足修胎等工艺进行一一比对,就可以梳理出元代青花瓷演变发展的清晰脉络。还有数枚写有“洪武元年”、“洪武三年”、“皇明建文元年捌月”、“正统元年”、“景泰元年”、“泰昌元年”等款识的青花瓷片,也足以襄助我们考察明代初期与黑暗期青花瓷器的工艺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状况。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陶瓷专家杨震华女士认为:“这些瓷片弥补了这一门类研究的空白”。
陶瓷的年代确定是一道难题,但是通过书中多枚元青花瓷片上“元至正元年三月初三”、“元至正四年”、“至正八年岁次”、“元至正十年岁次五月初五王备”等题款,再与瓷片的胎骨釉子、旋足修胎等工艺进行一一比对,就可以梳理出元代青花瓷演变发展的清晰脉络。还有数枚写有“洪武元年”、“洪武三年”、“皇明建文元年捌月”、“正统元年”、“景泰元年”、“泰昌元年”等款识的青花瓷片,也足以襄助我们考察明代初期与黑暗期青花瓷器的工艺特征以及与此相关的社会状况。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古陶瓷专家杨震华女士认为:“这些瓷片弥补了这一门类研究的空白”。
 瓷片对于我们进一步考察陶瓷的工艺特征也是极有帮助的,甚至比完整器更容易辩识胎骨的疏松与坚致、釉面的肥厚与莹薄、窑炉的温度、气氛以及工匠淘炼、利胎、修胎、施釉方法等。比如从本书所列数枚汉晋唐宋时期的残件与瓷片,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绞胎与北宋绞胎的纹理特征与造型趣味,唐代长沙窑执壶上的贴花图案又是如何将异质文明带入中国的,从唐代越窑盏托残件上的划花“年轮”又可以估计当时辘轳车的常规转速,从北宋定窑白釉印模印牡丹花碗残件外壁上可以清晰看到用于鉴定关键依据的“泪痕”,还可以从定窑紫釉残件上看到白胎上有一层黑色护胎釉,而且表面紫釉比护胎黑釉更薄,据此可判定为定窑器中极具研究价值的稀有品种。
瓷片对于我们进一步考察陶瓷的工艺特征也是极有帮助的,甚至比完整器更容易辩识胎骨的疏松与坚致、釉面的肥厚与莹薄、窑炉的温度、气氛以及工匠淘炼、利胎、修胎、施釉方法等。比如从本书所列数枚汉晋唐宋时期的残件与瓷片,我们可以看到唐代绞胎与北宋绞胎的纹理特征与造型趣味,唐代长沙窑执壶上的贴花图案又是如何将异质文明带入中国的,从唐代越窑盏托残件上的划花“年轮”又可以估计当时辘轳车的常规转速,从北宋定窑白釉印模印牡丹花碗残件外壁上可以清晰看到用于鉴定关键依据的“泪痕”,还可以从定窑紫釉残件上看到白胎上有一层黑色护胎釉,而且表面紫釉比护胎黑釉更薄,据此可判定为定窑器中极具研究价值的稀有品种。
 元明清三代,器物的装饰成为时尚潮流,底部由此成为鉴定的关键。从底足可以考察修足方法、胎骨质地与写款风格,器物内的图案,则在底部中心最能表现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时代风气。本书中这三个朝代的残件也多以器物底部为多,比如碗、盘、盆、杯的底部,以文字和图案来承担这样的使命,也为陶瓷爱好者积累这方面的知识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元明清三代,器物的装饰成为时尚潮流,底部由此成为鉴定的关键。从底足可以考察修足方法、胎骨质地与写款风格,器物内的图案,则在底部中心最能表现作者的创作意图与时代风气。本书中这三个朝代的残件也多以器物底部为多,比如碗、盘、盆、杯的底部,以文字和图案来承担这样的使命,也为陶瓷爱好者积累这方面的知识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

 图案方面,我们饶有兴味地看到诸如“醉仙”、“双雁图”、“双狮图”、“团花湖石”、“骑马访友”、“富贵有余”、“仕女游春”、“鹿衔灵芝”、“月下苦读”、“卧冰求鲤”、“莺莺拜月” 、“昭君出塞”、“五福捧寿”等,一方面以散发着市井气息的图像起到了传承民俗与礼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民众历经战乱后祈求太平的普遍心态。而在“高士观星”、“天马行空”、“指日高升”、“高冠厚禄”、“魁星点斗”、“高台修禅”、“英雄独立”、“羲之爱鹅”、“独占鳌头”等图案中,则更多地表达了知识阶层的理想情操以及对底层社会实施教化的意图。如果纯粹从美学角度来审察,这些碗底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比如萝卜、山猫、湖石、双鱼、翼龙、竹叶小鸟、婴戏图、蹴踘图等,工匠往往以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活泼的形象,呼之欲出,可亲可爱。
图案方面,我们饶有兴味地看到诸如“醉仙”、“双雁图”、“双狮图”、“团花湖石”、“骑马访友”、“富贵有余”、“仕女游春”、“鹿衔灵芝”、“月下苦读”、“卧冰求鲤”、“莺莺拜月” 、“昭君出塞”、“五福捧寿”等,一方面以散发着市井气息的图像起到了传承民俗与礼教的作用,另一方面也表达了民众历经战乱后祈求太平的普遍心态。而在“高士观星”、“天马行空”、“指日高升”、“高冠厚禄”、“魁星点斗”、“高台修禅”、“英雄独立”、“羲之爱鹅”、“独占鳌头”等图案中,则更多地表达了知识阶层的理想情操以及对底层社会实施教化的意图。如果纯粹从美学角度来审察,这些碗底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比如萝卜、山猫、湖石、双鱼、翼龙、竹叶小鸟、婴戏图、蹴踘图等,工匠往往以寥寥数笔勾勒出生动活泼的形象,呼之欲出,可亲可爱。
 青花碗底还常以文字点缀,而入选的关键文字常以“福”、“寿”、“状元及第”等居多,如从书法角度考察,虽然逸笔草草,龙飞凤舞,但无一笔不按照书法的行笔规律来完成。
青花碗底还常以文字点缀,而入选的关键文字常以“福”、“寿”、“状元及第”等居多,如从书法角度考察,虽然逸笔草草,龙飞凤舞,但无一笔不按照书法的行笔规律来完成。

在中国古代,匠人地位低下,居于社会上层的文人对“劳力者”的生产实践又比较轻视,所以古籍中对瓷器、玉器、木器、铜器、金银器、织绣等生产工艺的记载极为稀少。明清之前,匠人姓氏和制作年代出现在工艺品上的情况极为罕见,这为今人考证器物的产生年代与社会背景,布设了许多盲点与难点。但是,文物环境提供的信息还能为我们提供管窥蠡测的路径。比如相当一段时间以来,不少人认为在宋代与明代之间,应该有蓝底白花的瓷器存在,尤其是冯先铭先生已经试探性地提出元代青花瓷的概念,但事实上,许多人还是将这一时期的青花瓷器当作明代永宣时期所出的粗陋产品。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人约翰·波普通过对英国、伊朗、土耳其等国博物馆所藏数十件青花瓷器的考察,撰写了《14世纪青花瓷器:伊斯坦布尔托布卡普宫博物馆所藏中国瓷器》一书,尤其是他还以英国大维德基金会收藏的一对写有“元至正十一年”纪年题记的象耳大瓶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让国内专家有如梦初醒、醍醐灌顶之感。

元青花象耳大瓶残件
十几枚瓷片,将中国青花瓷烧造的年代向前推进了九百年。小小瓷片就像一根扛杆,以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为坚实支点,撬动了中国陶瓷史、中国美术史以及中国外贸史。
故宫博物院专家冯先铭先生曾经透露,在境外有三件完整的唐代青花瓷器,一件为香港冯平山博物馆收藏的条形纹三足鬴,一件是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花卉碗,一件是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后来我从多种考古书籍中得知,在伊拉克撒马拉地区曾有类似的唐青花瓷片出土,现藏于伦敦大英博物馆内。过了数年冯先生又透露,在海外又“发现”了两件唐代的青花瓷器,一件是美国波士顿博物馆收藏的花卉纹碗,另一件是丹麦哥本哈根博物馆收藏的鱼藻纹罐。

清光绪矾红釉描金双龙戏珠纹大盘
(二)
沈胜利先生精通玉器、瓷器、字画以及杂件鉴定。他19岁就进入上海市工艺品进出口公司工作,在组织安排下拜孙经品先生为师。孙经品先生确立师徒关系后即送了一枚瓷片作为见面礼,这是一枚杭州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瓷片,赏心悦目,釉色莹润,釉层肥厚,胎骨为烟极薄。沈老一直保存到今天,也曾让我观赏触摸过。孙经品先生早在民时期就研究瓷片标本,实在了不起。

明正统青花云山图扇面瓷板

元釉里褐彩龙纹残片
扬州同行喜出望外,后来还特意请南京博物院王志敏教授再行鉴定,认为沈胜利的结论完全正确,此物确系元代江西景德镇窑烧造的蓝釉龙纹梅瓶,国宝重器,世所罕见。现在,这件稀世珍宝陈列在扬州博物馆内,馆方为镇馆之宝设置了一个专厅,我几年前还特地去礼瞻一番。

元釉里黑童子纹高足杯残片
沈胜利一言定乾坤的那年,才36岁。未及不惑之年的沈胜利何以在元代蓝釉白龙梅瓶面前不疑不惑呢?这与他多年来一直通过寻访、收集、分析瓷片来进行古陶瓷研究有关。当年孙经品先生馈赠他一枚富有象征意义的杭州南宋修内司官窑的瓷片,等于给了他一把打开陶瓷文化宝库的密钥,后来沈胜利还经常请教苏州市文物商店专家张永昌先生和王志敏先生,两位都谆谆嘱咐他以田野考古方式收集瓷片,以拓展自己的眼界。从此他经常在赴外省市公干之余,在古运河、古码头、建筑工地等处捡拾瓷片,这些瓷片都成了他在上海文物商店当经理助理时辅导年轻人的标本,自己一片也没留。直到沈老退休后,才开始丰富自己的积累,寒来暑往,经年累月,也有近千枚珍贵瓷片入藏鉴古精舍。

明宣德青花卖花郎纹残片

金代褐彩虎形枕残件
(三)
今天,我们可以从《谈瓷侃片》这本书中获得什么呢?

明泰昌褐彩“泰昌元年”残片

唐黄釉绞胎杯

明弘治青花狮面纹残片

明景泰青花鳜鱼纹残片

明天启青花山雀图残片

明万历青花平步青云图残片

北宋磁州窑玉字纹钵残片
瓷片是文明的碎片,它给予我们残缺的审美体验。如有可能,或可请它来修订中国陶瓷史诗的韵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