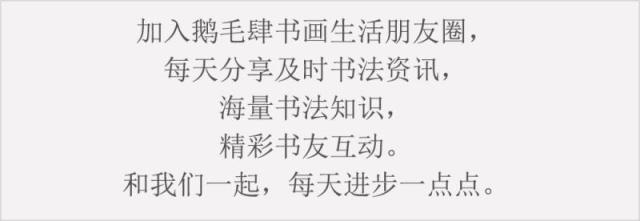卢辅圣|书法生态论

书法生态论
卢辅圣
也许,中国人是最爱讲道理的民族。就古雅者言,《老子》开篇即说“道可道,非常道”,孔子动辄即云“吾道”、“大道”、“有道”、“无道”。以今而俗者言,“生财有道”是对幸运儿的钦羡或奉承,“天公地道”是对买卖公平的炫耀或赞许,而“你讲不讲道理”,则是吵架和打架的序言。宋明哲学称为“道学”,也称“理学”。以此为界,讲理逐渐胜过道,到了如今,“真理”、“伦理”、“理性”、“理念”、“理智”、“理论”、“理想”等等既受惠于外来概念又脱胎于传统观念的新词汇,终于使原来似乎不难领会的道,变成隐没不彰、形同虚设了。
在以大量对偶范畴为思维杠杆的中国文化中,大概只有道和理找不到对立面。倘硬要找,那就只有“无道”和“无理”,实际上算不得正对应。但假如不拘泥于形式,那么,也能勉强找到一个,这就是“势”,高可对道,中可对理,低还可对法。势者,力也,权也,形也,情也,姿也,位也,睾丸也,总之,它是不讲道理法或曰道理法无可奈何的并且切切实实存在着的非原始亦原始、非继发亦继发的某种不可思议的动力。《说文》中没有“势”字,而以“艺”字通借,就因为后者也具有相类似的巫术涵义。
当历史长链在一代又一代人的具体规定之中延接为整合明天、今天和昨天的传统整体时,既显示为道、理、法的层次差序,而内向地收缩着自身的无限关联域,也呈现为某种不可逆和无所不在的势,而外向地开拓着自身的无限关联域。倘将前者称之为规律性,后者即是一种趋向性。规律不等于趋向。规律藏于内,趋向显于外;规律贯穿于全过程,趋向只指向一个时期和一个阶段 ; 规律是事物本质方面的固定关系,趋向则是事物变化现象定向特征的集合。例如地球的运动,不停地自转和公转,是贯穿其始终的规律,自寒而暖,自暖而寒,自昼而夜,自夜而昼,是体现其某一运动阶段的趋向。由于规律制约着事物发展变化的趋向,趋向于是反过来成为人们认识规律和把握规律的必由阶梯。
通过前几章对书法所由出的隐性文化和法、意的梳理,不难看到,既是操作,又是玄想,既是实用,又是审美,既是程式,又是修养,既是人心营构之象,又是天地自然之象,这双重性格,使得人们对书法艺术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对书法艺术的把握。
大凡事物与人所发生的联系,不外乎认识 ( 真 )、伦理(善)、审美(美)三种形式。三种形式决定了事物的三种属性:意义、实体、符号。当人的思维能力赋予事物以意义时,人就与之建立起认识的关系;当事物成为一种实体而为人所用时,人就与之建立起伦理的关系;当事物成为人的内在价值尺度的象征符号时,人就与之建立起审美的关系。审美不是实现人的现实个性对物质对象的评价,而是实现人的审美个性对符号对象的评价。换言之,美既非“主观与客观相统一”所能解释,亦非“主体性与社会性相统一”所能界定,前者是真(认识)的属性,后者是善(伦理)的属性,美之所以取得与真、善鼎立而三的独特地位,在于它通过主客体的交流运动形成一种非功利性的意象图式,可以(当然也可以不)与前二者发生分离甚至对抗,从而标志或展示了人的某种自由价值。
美是艺术追求的目的,然而艺术实现美的手段却是技术活动。美的不可重复性,使它成为本质上不是积累性的。技术则是一种不断积累的过程。一方面,作为一种社会共同财富的知识,不断落实为个性心理特征的能力,另一方面,又作为一种个性化能力,不断融汇成社会化的知识,在这个交叉过程中,人取得了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自由,所谓“法”,实际上就是以技术为载体的。“法”的体系的形成、发展和完善,是人的审美理想和表现能力高度统一的产物,从上文对历史的粗略梳理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但是,我们同时也清楚地看到另一个事实:在“法”的体系完善化进程中,技术理性以其必然而精确的单向深入能力,既推动着“意”奋勇向前,又给人的思想和心理带来不堪忍受的负担,直至成为禁锢“意”的封闭体。技术从实现美的手段僭越为目的,以其独立的实体横亘在人与艺术之间,致使人通向艺术的美失去了原先那种直接性、生动性和自主性。这就是人的本质力量非对象化的削弱乃至丧失。
非对象化和对象化,亦即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是一个过程的两个面。美的实现,既需要主体化的自由,又需要客体化的自由,前者使人的本质归属于人本身,后者使人有能力驾驭对象。早期人类,超脱个体而与属类合一,超越瞬时而与永恒神交,获得了极大的主体化自由;然而这种自由建筑在必然性基础上,正是驾驭对象能力低下的结果,因此对于客体化自由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随着历史进程,人越来越多地获得了客体化自由,同时也不知不觉地失去了主体化自由,以至每一个人都陷落在一个狭小的生态环境和语义环境之中,整体成了个体的异己力量。书法作为一种艺术,需要双重自由,但历史偏偏不随人愿,而使双重自由成“剪刀差”发展,于是,它们交换主导地位的时代便成了最有意义的时代——双重自由的相对平衡时代。
魏晋(灵性化)和隋唐(性情化)正是书法史上的这样一个特殊时期。魏晋是主体化自由为体而客体化自由为用,隋唐是客体化自由为体而主体化自由为用,因而前者取得了书法史上自然(中和)之美的极致,后者取得了书法史上人工(分刍)之美的极致。时间越往前,越是主体化自由压倒了客体化自由,故往往意(感性的直觉感悟)胜于法(理性的抽象把握)。时间越往后,越是客体化自由畸零主体化自由,故常常法胜于意。在主体化高度自由的时代,人们并不知道它的必要性,而一味追求着客体化自由;当客体化自由反过来威胁到主体化自由的存在时,主体化自由才成为人们追求的目标。于是,意胜于法,审美境界为“景”;法胜于意,审美境界为“趣”;法艺相权,审美境界为“境”。作为书法艺术的本体论内涵,是在双重自由度的严格保障下而得以实现的。当主体化自由主宰着客体化自由之时,客体化自由逐步强大的过程也就是书法艺术逐步走向本体化的过程;当客体化自由强大到转而主宰了主体化自由之时,主体化自由逐步削弱的过程也就是书法艺术逐步走向非本体化的过程。本体化从非书法(文字、美术字、书写或绘画等等)的混沌状态中解放出书法艺术的因子,组成逻辑形式的自调中心,从而走向独立自主,以其自足的实体雄踞于艺术之林。非本体化则使书法泯灭自己与非法书法的界限,瓦解逻辑形式的自调中心,从而化整为零,变有(此物)为无(他物)。简言之,本体化过程是增加有序度,抟多元为一元,亦即书法艺术王国的建设过程;非本体化过程却增加无序度,破一元为多元,亦即书法艺术的解体过程。以魏晋隋唐为峰巅,书法艺术发展史呈示出先于此的本体化(上行)和后于此的非本体化(下行)的慢慢长坡。
然而,这座书法本体论的大山,尽管承载着有史以来从事书法的攘攘众生,却从不肯把它的真实面目坦露出来。“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用苏轼这首诗来描述认识与实践的矛盾,恐怕最恰当不过了。书法必须通过层出不穷的个人行为求得自身的发展,而任何个人都只能在历史条件局限下的极小范围内施展自己的聪明才智,用一个个人连结成的历史长途,向着未知世界逶迤铺展,书法就踩着它不断前行,每一步都是确切无误的,在总体上却是盲目无知的。人们对于事物的感知和追求,无不建立在一种“完形”心理和“逆反”效应的原则上。莱根的真正香味,只有吃厌了鱼肉的人才能会得。潜意识的重大发现,只有在理性统治了整个人类的情况下才具备条件。书法史上主体化自由和客体化自由的对立,是随着主体化自由丧失程度的加深而加深的。庾肩吾《书品》云:“王工夫不及张,天然过之;天然不及锺,工夫过之。”这是双重自由相对平衡时代对法意统一境界的理性把握。到了张怀瓘《书断》“先禀于天然,次资于功用”,就开始侧重于主体化自由的追求了。时至朱和羹《临池心解》,所 ' 谓“学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对主体化自由的追求已成极则。但是,如同前面梳理书意的发展轨迹时所看到,当人们越是把信仰支点从外部移到内部,移到一个个性的主体,本质意义上的主体化自由却越是丧失它的主动权。操作与玄想,形式法则与审美观照,或者说,表达作者情感和创造稳固形式,始终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一旦这个集合体为人及其书法的自觉意识所肢解,人与书法就同样失去了平衡,患上了“精神分裂症”。一方面,客体化自由的不断提高,使人的摹仿、取用、创造能力和认知本质力量包括审美本质的能力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另一方面,主体化自由的不断觉醒,使人的精神情感从上述能力中分离开来,把个体性情作为一个与之相对立的认知和审美标准;两者之间鸿沟的不断扩大,又使书法陷入了一个悖论的无底洞——作为一种审美观照,一种表达情感的需要,那么,创造稳固形式和遵循形式法则的愿望是多余的,作为一种艺术的创造,一种美的物化形态,那么,要想从中得到不折不扣的审美观照和情感表达,则是不现实的。说句极端的话,就是:既然是书法,就有书法的极限,任何从事书法的人都只有在极限中超越的自由,而不可能有超越极限的自由;超越了书法的极限,那就是对法的逃离或取消!
书法史上沿习千年而不废的“博采众长,自成一家”,正是非本体化发展时期遵循着这一原则的唯一有效的自我完善之路。博采众长也就是上一章所说的夺取他神,自成一家则是获取我神,两者之间的关系,不仅体现在自我完善的过程中,也同时体现在自我完善的程度上。他神要兼众长,就为书者规定了一个现实的起点;我神须成一家,则为书者规定了一个崇高的目标。人的自由方式和自由内容建立在共性与个性中和平衡的基础上,个体精神反射着群体精神,群体精神又体现着个体精神,既是高度个性化、自我化,又是高度传统化、属类化,这种追求本同而末异的认知结构和表现方式,导致了中国书法致力于纵向深入而不是横向扩张的独特发展方式。一点点细微的形式差别即可启示和引发人们的审美观照与情感表现,就杜绝了书法发展的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在客体化自由日益强大的进程中,把书家的主要精力和最高目标集中在精神追求而不是形式翻新上,从而使形式媒介取得自净的足够时间,避免了过早枯竭的危脸;二、在主体化自由遭受欺凌的境遇里,使个体精神在对群体精神的求同和依恋之中获得自我满足,从而优游在书法的极限范围内,避免了对极限的超越而导致取消书法的危险。隋唐以还,书法在非本体化的下坡路上之所以能保持自己从容不迫的步伐,而不至于一跤摔到深谷里去,根本原因即在这里。
然而只要时间不灭,一切价值系统终将面临挑战和危机。“博采众长,自成一家”的自我完善之路,必须在“天人合一”的价值取向和“得意忘象”的把握方式保障下,才能行之有效。也就是说,它必须建立在自然经济的基础上,必须以自然与自我的和谐统一以及由之产生的蕴而不躁的审美观念为主导,必须乞灵于既是情感化又是理性化、既是个性化又是共性化的认知方式和表述方式,而且必须使这一切都纳于由之而不知之亦即习惯成自然的惯性系之中。因此,久而久之,势必暴露出一个无可回避的缺憾——不可能把人从历史的受动客体变成历史的能动客体。对于业已分离并且不可逆地对立着的客体化自由与主体化自由,对于随之而发生的悖论无底洞,它都是用消极和谐的方式维持偏安局面的,既无力抵御客体化自由对主体化自由的悍然进犯,也无法消除悖论无底洞的潜在威胁。一旦自然经济的基础发生动摇,人工经济所特有的积极进取精神便挟带着科学理性的价值观和形式逻辑的方法论长驱直入,他神和我神,众长和一家,共性和个性,传统和创新,都将从中和平衡转向割裂对抗,书法发展的纵向深入的堤坝,也将随着在横向扩张的洪水巨浪中塌方崩溃。
如果说,明清此起彼伏的异端派更多的是出于对求同风格的叛逆,而缺乏强有力的文化反思作支柱的话,那么,近现代书法史上形形色色的变法创新活动,则是在西来文化冲击下逐步上升到理性文化层次上反思的对旧传统自足系统的全面冲击。当然,我们不能无视于这样一个事实:因为书法内涵的特殊性,它只是被偶然地催发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文化形态,故并不存在外来同类艺术的正面冲击。由于这个原因,它往往成了历次文化革命运动的逍遥派,既避免了中国绘画被反映论所陵替和中国戏曲为斯氏表演体系所异化那样的噩运,同时也失去了站在更高的文化层次上进行反思时所必需的异域参照系,以至独往独来,无声无臭。毛笔退出实用性的历史舞台,和“文革”中打倒一切的十年浩劫,对于书法的打击也不过坐了坐冷板凳而已。但是,正如中国传统的自我完善之路只能在中国传统自然观的保障下才行之有效一样,逍遥派的日子,只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并未危及中国传统生存方式和观念形态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存在。新时期以来,随着改革开放浪潮的高涨,人们从物质生活到精神生活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书法这块以不变应万变的“飞地”,也就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强烈的震荡。
艺术品,尤其是视觉艺术品,大都具有跨文化的意义。完形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不同的人在观照特定形式时,心理上会产生与之同构的反映,产生互相类似的感受。但这种跨文化的意义毕竟是有限的,人们在观照一个对象时,除了形式造成的心理反应以外,还受到自己所处的特定观念、特定文化背景的制约和诱导。应该说,一件艺术品只是一种元素,当它和其它各种元素结合在一起时,才变成一个功能单位。书法之所以成为一种艺术,不仅因为书法本体具备了艺术的功能和艺术的特质,更大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文化赋予了书法以艺术的功能和特质。日本书道是中国书法的移植,要保证它的繁衍发展,如果彻底脱离汉文化的土壤是不可思议的,前卫派虽得力于西方抽象画,也不过是中西文化并协的产物。中国书法面临的强烈震荡,和日本书道业已经历并且正在继续的震荡是同性质的——一由于传统文化模式的崩坏,原来固定为一功能单位的文化丛亦随之崩坏了,人们对书法艺术形式的读解和需求,出现了相对自由的倾向。具有传统文化修养的人,照例依据传统的惯例去领会和使用形式下面的意义;对传统一知半解的人,则依据他们所具有的文化惯性去承受对传统形式的偏好;接受了更多时代文化亦即西方传播文化的人,开始从现实时兴文化的立场上对古老形式作随心所欲的阐释和改造……如此种种,汇为一股“剪不断,理还乱”的多元化潮流,拍打着与书法有关的每一个人的心灵。可以想见,在新旧文化或者说中西文化激烈交锋、交融、拉锯反复、相持不下的特定历史阶段,书法所面临的多元化的混乱局势是无法改变的。
问题不止于此。倘若仅仅是中西文化的横向交叉导致了书法的内部震荡,书法未必会面临全面而深刻的危机。现在的棘手之处,在于这种震荡发生在书法自身严重的非本体化进程中,内的虚脱和外的冲击集中在一道,稍有不慎,便罹一蹶不起之灾。不要以为这是危言耸听,在当前书坛繁荣热闹的表象下,确实潜伏着危若垒卵而不是居安思危的某种不祥之兆。
创新这扇艺术发展的羽翼,越往后,越是为人们自觉利用,奉为至宝。如前所述,在仅仅关注于风格变革的层次上,创新与守旧的对立不过是殊途同归。那么,乘驾着当今变革潮流的“书法热”,情况又是如何呢?尽管我们看到,书法作为一门艺术的自觉程度和普及程度,是任何以往的时代所无法比拟的;从局限于风格变革的狭隘圈子里挣脱出来而向着观念变革的更高层次升华也已经开始了确切可见的步伐;在东西文化交流的磅礴背景上,人们赖以反思的思想基础和物质条件,更具有迄今为止最大的优越性……然而,只要摘掉庸俗社会学的有色眼镜,真正站到书法本体的立场上,我们便不能无视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创新这扇光明的羽翼之下,正播散着自我破坏的巨大阴影!
自从以沈尹默为代表的正统派对清代北碑书风实行规模不小的回潮之后,作为现代书坛的主要支柱,不论表现在风格上还是观念上,都基于继承、修养、实用三位一体的复古主义立场。但即使是二王的儒雅旧途,从审美意识和创作观念的正宗性言,也在不断地淡化、瓦解,前人凝结成的规范法度,逐渐为各取所需的理解和实践所替代,传统这个为绝大多数人所重视的概念,内涵在缩小,外延在扩大。其中偏于保守的一翼,较多地局限于一家一派的灵活选择;偏于开放的一翼,或致力于纵向的继承性,或致力于横向的贯通性,显示出更灵活、更不拘一格的时代特征。
如果以上称为传统派,那么,与之相对的所谓现代派,则直接从观念变革入手,对“正统”甚至于被公认的一切典范进行公开反叛。他们是一个信念趋同而目标散乱的集合体,艺术主张上的分歧,与其说表现为与传统派之间的,还不如说表现为创新范围内部的更加确切,因为对于前者,只要掌握对立原则——前所未有就行了,对于后者,主观选择的恣意性可以带来失去标准之后的一切混乱和自由,而且这种混乱和自由,势必随着现代派的自成气候而加深、扩大。
人们往往执着于肯定传统与否定传统之争,其实,这不过是一种极为表面的现象。肯定传统的并非不会在不自觉之中蜕变传统的精华,否定传统的也说不定会在更深一层意义上光大被掩埋了的传统。问题的实质不在于口号、目标,而在于行为本身。倘若揭开这个盖子,就能在形形色色迥然异趣的表现之下,发现同一个持续不变的趋向——放大媒介行为。
媒介,在我们这里,是一个特指的概念。一般它泛指使有关双方发生关系的人或事物,我们则将之进而区分为内同型和外同型,并把外同型狭称为媒质,内同型特指为媒介。所谓外同型,即主体感觉联系于外在事物而表现为杂多性的暂时同化效应。所谓内同型,即主体感觉体现了目的追求的统一性的泛时同化效应。外同型所采用的媒质,比如绘画中的题材、形色,书法中的字形、黑白等等,必须通过内同型内化为高度类型性的媒介,例如绘画中的构图、造型、笔触、色调,书法中的点画、结体、章法、神彩等等,才能真正实现为表现。
从魏晋的中和,到隋唐的两极化,从南帖的婉媚,到北碑的犷达,从无意而璀灿自呈的甲金文,到奔蛇走虺一泻千里的狂草,从刻意求新的颜柳苏黄,到惊世骇俗的金农郑燮,都可以看到媒介被强调使用的痕迹。照理,审美能力的加强对于媒介利用率是个促进的过程,但由于情感表现的自觉程度也随之加强,媒介的消费量反而远远赶在前面,形成了一个审美能力愈强愈需要强化媒介的循环圈。在纵向深入的传统发展方式保障下,人们习惯于或者致力于同媒介的再生作用,因而长时期地维持着生态平衡。自从横向扩张的发展方式取得主导地位以后,立足于物质本原的元素构成观点的对事物作理智化、逻辑化、定量化分析的西方方法论被定于一尊,对于媒介潜能的开发成了自觉和自如的行为。与此同时,书法自身的极限迅速显现出来。传统派自觉地遵守着极限,现代派勇敢地冲决着极限,但无论如何,像农业经济时代那样的人与对象的和谐关系已经不复存在了,代之而起的是人对对象的占有、驾驭、改造,是像工业经济时代那样的人与对象的对立关系,区别仅仅在于传统派搞的是“民族工业”,现代派搞的则是“世界工业”而已。审美能力愈强愈需要强化媒介的循环圈,此时百倍千倍地加速运转,媒介蕴含的能量犹如石油般地被竞相开采,并且制成千奇百怪的新产品。在“民族工业”那里,颜书的雄强意蕴可以变成霸悍作风;米字的八面锋可以演为仰卧起倒的任意用笔;摩崖石刻上被苔蚀风化的斑斓点画,可以膨胀为受用一世的个性标志;从求同(神似古人)趋向求异(别于他人)的时代感召,可以把艺术朦胧时期人们在摸索中留下的一切形式因素作为各自创新的支点。在“世界工业”那里,抽象与具象的灵活把握,可以使书法随便出入绘画领地;审美空间的大胆开拓,可以使书法跻身于装潢工艺的行列;色彩、新材料和新工具的运用,更可以使书法担负起软笔、硬笔、刻刀、电烫以及写、印、刻、塑、绘、泼、扎、铸等等永无止境的实验性功能。凡此种种,不一而足。媒介的选择基点和放大程度,往往成了检验个性和创新程度重要甚至首要的物化标尺。
硬笔取代毛笔的时代变迁,对书法所依存的土壤固然是一种破坏,但还不是关键因素;关键在于放大媒介的行为本身直接导致或者基于一个“简化模式”,使书法在观念和性情的一只脚以外失去了毅力和功力的另一只脚。“简化模式”无休止地简化着表现方法和表现形式,大规模地吞噬着媒介的潜在生产能力及其滋生地,超高速地刺激着社会的价值观念和消费水平,种种未知的物质和能量,都飞快地变成创新的鲜果,然后又飞快地沦为一日色变、二日香变、三日味变的陈货。艺术角逐将异化为商业竞争,自变原则将异化为自否原则,变法周期的短缩,审美生态的失调,艺术功能的衰竭,将随着书法市场的扩大而递进。由此指向的唯一前途,将是书法非本体化进程的加速完成——站在书法本体论立场上,也就是书法的消亡!
亮出“消亡”这个字眼,是会惹众怒的,因此必须对此有个注解。所谓消亡,并非一事物的消失,而是一事物的本质被异化、肢解、播散,成为另一本质的他事物。用系统论的说法,即并非该系统的各层次子系统全部解体,而仅仅表现为主要层次结构的全部或部分解体。一个国家消亡,家庭组织依然存在。一个生命体消亡,大量物质元素也依然故我。书法的消亡,说明人的审美个性对符号对象的评价关系变成了人的现实个性对物质对象的评价关系,或者人的审美个性对书法对象的评价关系变成了人的审美个性对绘画、文字等非书法对象的评价关系。换言之,亦即书法的实体和意义功能遏制了符号功能,或者书法的符号功能纳降于绘画等别的艺术门类的符号功能。现代派把书法的未来憧憬为“世界性艺术”的迷幻图景,实在是忽略了事物存在着质的区别之故。传统派对“继承中创新”的半推半就的改良口号表现出盲目乐观情绪,也同样基于“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局限性认识。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基础:决定论和实用理性。前者认为书法的发展是由低向高、由谬误向正确前进的永恒过程,却从根本上忽视或者否定了书法自身的发展极限,因而在这个“终极真理”光照下的所谓遵循客观规律,实际上只能是各人意志和目的的盲目幻觉。
后学是对前者自觉接受的结果,即不自觉地把自己交给了一种“行为迷信”——往前走就是光明的路,因而“每一步都是确切无误的,在总体上却是盲目无知的”,始终走不到“庐山”外面去。
其实,平心而论,这一切又何尝不是客体化自由畸零主体化自由而导致的主体的超越行为!人们对艺术的认识远远落后于对艺术的把握,就因为置身其中者总是以本体的理想为转移,置身其外者又总是以非本体的眼光看待本体,永远得不到互补和统一。只有能深入其中又能超脱其外的人,才具有认识本体、把握本质的气度和能力。只有摆脱个体利益的狭隘观念,关心整个属类的前途命运的人,才有可能真正站到人类文化的高层次上进行思考。同时也只有在伟大的变革时代,才能赋予思考者以批判思维的特征和理性思辨的品格,从而为减少认识上的心理眩惑驱除迷雾。道的隐没不彰,和势的日渐显明,使旧的艺术模式在不断地松弛、塌坏,人们的艺术精神在获得自由解放的同时,也感到了迷茫困惑、无所适从的苦闷,惯常意义上的自我见解、自我信赖、自我选择、自我设计,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和冲击。然而,恰恰在而且也只有在此时此刻,我们终于获得了一个瞻前顾后、全面反思和重新定向的大好机会。
卢甫圣|亦署辅圣。 艺术家、美术史论家、出版人、文化学者。浙江东阳人,现居上海。毕业于中国美术学院中国画系。现任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上海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上海书画出版社总编辑、朵云轩总经理,同时兼任《书法》、《朵云》、《艺术当代》、《公共艺术》等刊物主编,中国美术学院、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等校博士生导师,上海中国画院画师。著有《天人论》、《书法生态论》、《中国文人画通鉴》、《中国画的世纪之门》、《中国文人画史》等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