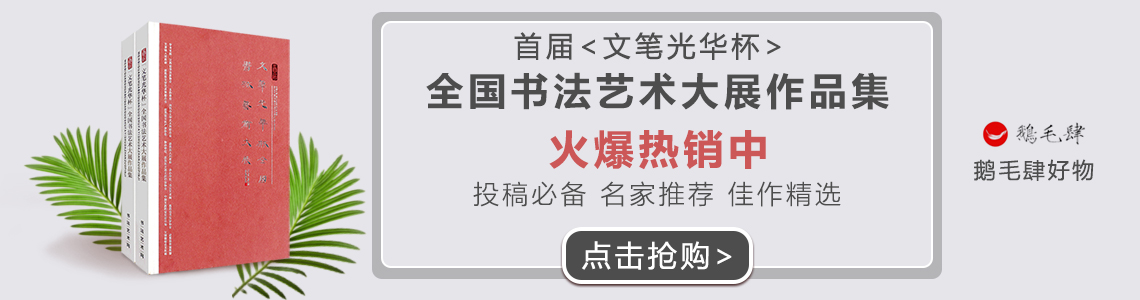中国书法与古代建筑
2020-08-17 09:23:38 来源: 点击: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站在这些千古年来绵延存活下来的伟大艺术品面前,我们是不是该静下心来,怀着一丝的敬意,去努力理解蕴涵其间的“遗传编码”,去参悟这份遥远的虔诚和妙思,去阅读它们无声地传播给我们的价值和意义?

人们常说“书画同源”,其实何止书画,人类的一切艺术形式都是同气连根,互动互通的。清代书画大师石涛尝云:“太古无法,太朴不散;太朴一散而法自立矣。”正道出了包括艺术在内的所有有“法”的事物都基于共同本源的事实和规律,至于什么是这个“无法”的本源,用《道德经》的术语来讲可以称之为“道”。这一点老子早已认识的很清楚,“朴散则为器”,“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当然,归结到人类的艺术上面,情况更加复杂。要在一篇文章中分析所有艺术之间微妙内隐的关系也是绝无可能。我们只能捡拾起一些浩瀚艺海中闪光的贝壳对比把玩,并努力探究其间易为人们忽视的“势态”的奥秘,也算对得起创造下这些美仑美奂瑰宝的祖先。本文要说什么呢?说书法和建筑。

(一)朴素和材质
“朴散则为器”,什么是朴?老子经常说圣人要“见素抱朴”,素是指未经染色的丝绸,朴是指没有加工的木材。一言以蔽之,原材料是也。中国古人历来讲究“五行”之说,金、木、水、火、土,构成人们心目中最原始的世界的本原印象。五行是中国人世界观中万物组成之基本元素。
建筑与书法,在这个基本元素的起点上,就密不可分了。中国的建筑,有别与西方建筑的第一大特征,就是建筑材料的选择上。西方的古代建筑,无论埃及的金字塔,罗马的斗兽场,希腊帕台农神庙,圣索非亚大教堂,都是以砖石为材料建造的。西方人要以这种强悍粗犷的材质彰显人类改造自然的伟力,并冀望人类文明的永存。而中国的古人却持着根本迥异的思路:从来不相信天地间万物之永恒,“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主流思想是顺其自然,人不可胜天(荀子是个例外),因而,在建筑的材料的选择上采用了温柔质朴的木头。这种材质自有其独到的优点,首先是它的轻便及由此带来的防震性(因为承受屋顶重量的不是墙壁而是立柱),其次是其采伐的便宜性,可以就地取材(古代林木繁茂不比今日),再次是它的可再生性,用现代话讲就是生态的可循环性,即使经年腐坏或焚毁也很方便原地推倒重来(中国人重视故土难离)。可见中国建筑的基本元素是五行中的“木”和“土”,正所谓建筑学谓“土木工程”,旧称帝王将相的建筑施工为“大兴土木”。
至于书法,文房四宝,笔墨纸砚无一不与“土”及“木”相关。笔的秆子是竹子或木头斫成的,甚至有的笔全部由“木”构成,如竹笔,蒿笔;墨更不必说,《述古书法纂》载:“刑夷始制墨,字从黑土,煤烟所成,土之类也。”,还有一说是某日刑夷在河边洗手看见水中漂来一松炭把手染黑于是带回家以粥饭和之,凝结成状,此为制墨之始。不管怎么说,墨仍然属“土木”;纸,大家都知道是我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以树皮、竹纤维、藤革等为原料制造的;至于砚,无论端砚、歙砚、红丝、澄泥四大名砚,还是远古时期的石砚,陶砚,都离不开“土”。
这是从最基本的材质上说起,关键在于艺术的创作过程。在运用由这些材料制作的工具或元件进行艺术的创造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拿西方同类或近似的情形作下对比。在西方,关于书写,也有penmanship 和calligraphy之说,大体含义是指书写的流畅工整与否,和我们的书法或日本的书道决然是两码事情。所以我们翻译时常常不得不加一个“中国”的字眼,唤作“china-calligraphy”,实在是不得以而为之。即便如此,也常常造成误解,尤其是对于本来就对艺术不甚了了的外宾而言。一次在酒吧我跟两个外国朋友说关于书法的话题,我说了句calligraphists deserve honour and rewards(书法家理应获得尊荣与回报),他们听了直摆脑袋带着惊疑的神色。也难怪,在他们眼里,西方的calligraphists 就跟calligrapher(抄写员)一个涵义一个地位。所以这得谈到东西方书写工具的不同,西方的pen盖缘于羽毛笔,虽然很相似于我们的毛笔(禽兽之毛,如苏轼还用过鸡毛笔,王羲之还有鹅毛笔),但起点意图就不同,情趣更不可同日而语。总体来说,西方人用笔是为了记录,传达信息,只图个方便快捷,所以越发展越和中国的书写性质背道而驰。中国的文人和官员们在传播交流信息以外,更注重生活的修身养性,流连于人生的况味(与中国人的处世哲学和儒道精神有关)。于是本来记载信息的普通工具,具有了艺术传播的功能。之所以能够具备艺术性生产可能的前提是毛笔的“柔翰”品格。这又回到老子所谓的“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上来。刚柔并济,柔中带刚的品性使得运用毛笔可能发挥更广阔的作用。而另一个重要的元素便是书法创作中极其重要的材料——水。
由于有了水,使得毛笔下的线条灵动活泼起来,表现力有了无穷的变化。毛笔的特性,水墨的交融,中国的艺术家们在一册册竹简一张张白纸之间应运而生。相对观之,西方的笔,即使是用来作画的笔(brush)也被看作是“刷子”来用,基本没有线条的表现空间,但以色彩光影形象透视为长,有的基本只是涂抹,而涂抹所用之颜料,是动物胶,矿物植物等化学提炼加工的东西,水在这里只作为调和的“溶剂”,在整个画面的创作和完成中,你无法看见水的流动。中国画和书法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水,是中国书法的“精气神”的物质源泉。
而同样地,在建筑作品中,水几乎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典型的苏州园林景观中,曲水、清溪、莲池,随处可见,是园林建筑中必不可少的构图元素,这里没有了水就跟书画中的一律的“枯笔”一样,虽然也可以造成审美的效果,毕竟将大打折扣。而在规模最为宏大的北京故宫建筑群中,本就无水的诺大场地,硬是被设计者生生挖出了一道护城河,挖出的土堆成了一座景山。因为中国人讲求好的“风水”,依山傍水是最理想的居住环境(即使人死后的墓地最好也要面水背山以利于后辈人丁兴盛),水在一组建筑群体中,仅就其艺术价值而言,是不可替代的。建筑师用如椽巨翰蘸水一挥,原本沉郁的楼阁院落厅堂广场刹那洋溢着飞扬的灵性。
当年书圣王羲之等士人“群贤毕至,少长咸集”,“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幸好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才更能够有兴致“俯仰一世”,“放浪形骸之外”,激情挥毫写下千古绝唱的第一行书《兰亭序》。有兰亭,有曲水,有笔墨文章,五行具备,此乐何极?

(二)几何与造型
这里的“几何”内涵取自然科学中的学科“几何学”的概念,不是我国古人的感喟“人生几何”云云。总之是与造型相联系。
中国的古代建筑是个什么样子呢?同西方建筑对照概观,我们的建筑基本都呈现一种矩形的几何形状。矩形即长方形,简洁、单纯、平整、中规中矩。长城是长方形的,紫禁宫是长方形的,十三陵是长方形的,岳庙是长方形的,岱宗坊是长方形的,武侯祠是长方形的,四合院是长方形的……而西方的建筑,不管规模如何,总要带一个穹顶,至少也要避免方方整整的规矩模样,或者把脑袋削尖,或者全身雕刻满凸凹的花纹和突出的形象,要么干脆选择耀眼的几何形状。于是,金字塔是三角形的,罗马斗兽场是圆形的,教堂的头顶尖尖的,朗香教堂根本说不出是什么形来……中国这样的建筑里面也许正适合了居住这样的人们,人们的生活简单、朴素、等级严谨、法度森严,不越雷池一步。也很象中国人的脸,蒙古人种的脸和西方人相比,是扁平的,缺少变化的,相对稳定而明晰的。而一种质朴、明白、简练的性格也正由此昭示。
就象经常被提出与西方的哲人柏拉图并论的我国的圣贤孔夫子所著的《论语》一样,它的语言也是简洁明了,直白规矩的。比这更简要的是《道德经》,只有五千言。中国的语言是矩形的,读起来宛如抛出一块接一块的砖(当然是指文言文),字正腔圆,铿锵有力。不似英语吞吞吐吐舌头打转,仿佛声音绕着白宫的圆顶子盘旋不休。
而说到书写上面来,同样如此。拉丁字母反复缠绕,几何形象就跟其建筑一般无二,弯曲圆团,联贯书写起来更是如哥特式教堂运用的飞券和玻璃的花纹,巴洛克风格建筑上面华丽的浮雕,密密麻麻一扫而过。而汉语及汉字,不仅发音方正,字型更易发觉,横平竖直,一丝不苟,世谓“方块字”,盖因其形。而整体看上去,一幅《张迁碑》、《神策军碑》、《多宝塔碑》不考虑其艺术赏析效果,都是整整齐齐。黄庭坚说,作楷书当如“快马入阵”,单从表面掠观,不正是如同中国建筑那样的矩形几何状吗?古代的排兵布阵,在未有变化之前,阵形一般不都是长方形的规整吗?
法国学者罗兰·巴特在描绘日本人的面孔和眼睑时说:“那种模式不是雕刻性的,而是书写性的:它是一种柔顺的、轻弱的、交织紧密的材料(当属丝绸一类),干脆的说,似乎是被两条线顷刻之间一挥写就的。”抛开他审视描绘对象的局限性不说,对于东方人外貌这种“书写性”的发现和修辞倒是颇有意味的。这让我想到中式的那些古老的建筑(也可以包括一些日本的类似风格建筑),在精神层面倒是的确和人的气质很相通,就是那种大气的,淳朴的,简洁的特质,毫无遮蔽性,公开而恢弘,平实而慎重。这跟西方人外貌尤其是眼睑部位的深邃、神秘,及同样地,建筑风格的精雕细琢繁琐芜杂和幽深伟岸迥然不同。中国古代的建筑,的确,如中国的书法一样,是谨怀法度,一丝不苟,但却毫不犹豫地在平面(空地或宣纸)之上,“一挥写就的”。
的确是“一挥写就”。法国凯旋门的建造花了30年,同期乾隆皇帝兴建占地22公顷的普陀宗乘之庙,只用了4年。

(三)标志和隐秘
大屋顶,是中国古建筑在形态上所独有的特征,也可看作是中式建筑风格的最显著标志。由于是木制结构,梁、椽、檩互相搭构交叠,屋顶相对来说就会显得大一些。更主要的是,这种大屋顶,常常不是直的平面形的,而是曲面形的。屋檐是曲的,屋脊可以是曲的,屋面都成了曲的。这样的大屋顶,屋檐都伸出房屋很远,有的甚至直冲云天。这样就给略显沉闷的屋顶及整个建筑平添了生动,避免了呆板和僵硬。正如古代文人所形容的那样:“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故宫三大殿和所有宫门那些一望无垠的金碧辉煌的硕大屋顶,虎踞龙盘,大气磅礴,气象恢弘。(关于大屋顶极其曲面形态的原因还有许多其它说法)
与建筑中显著的大屋顶相对应,书法里面,单字结构同样有一个重要的标志性笔画。那就是一画(横),永字八法里面所说的“勒”。这个“—”在中国文化中具有非常的意义,周易中以之表示“阳”,乃万物之始,所谓一生万物,圣人抱一。而一画在汉字中同样是最显著和独特的笔画。正因为有这个“—”的存在,汉字才所以能成为“方块字”。可以说,汉字的最大特点就突出地表现在这个“勒”上面。可以对比说明,拉丁字母从a到z的手写体,除了如a,c,e,o等几个字母呈现圆形特征外,其它字母至少有一半以上是竖长形状的,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英文词汇是横向排列组合,而且书写时也同样是横向书写的,因为字母的纵向性格决定其在构字(词)上必然采取横向的范式,进而形成横串的字(词)则也同样必须采取横向书写的方式。否则一来不方便,二来浪费书写空间,三来很不美观。相反地,汉字由于横画的醒目位置,使得文字外表上呈现方型的特征故而既适合横向书写,更适合纵向行笔,以在视觉上产生一种趋向于有活力的平衡感。横画的重要,还表现在它运用在起笔之始,起到建筑中先打好地基的作用。我们写字,正确的笔顺一般都要求是先写这一横画(没有横画的字当然除外例如“小”等字),为什么?这样可以一下笔就确立书写这个字的重心和整体走向,保证字体的平衡性。人体素描中有“三停五眼”之说,目的和这个道理一样,是为了找准位置,减少偏差。我们还会注意到这样有趣的一个现象,写单个的字是从左向右书写,而写整幅的字(即一篇书法)却是相反,即从右向左写。这里面有一个相扭的力。也许秘密就在这里。孙晓云在《书法有法》一文中认为,“这种书写习惯,书写程序,都是出于转笔的顺手。”,她是从笔法的视角作出解释。不错,就象我刚才谈到的那样,单字那种方型的横势,由于从上向下书写的纵势,才形成一种动态,一种反拧的张力。谈到字体及书写的纵势问题,有人也许会说,篆书比楷书成型早,形状可是修长的,更类似于拉丁文字。为什么也要从右往左从上向下地书写?问的不错。我们不妨再追溯一下,直到甲骨文和金文,其字多用横画,借以表象。都是纵向密布于甲骨青铜之上。对于这个问题历来考证欠缺,我有个想法是,这可能还有当时古人的书写条件和状态有关系。因为那时候人们没有案几桌椅,还需要以尖利工具在骨甲上铭刻。设想其书写形态应该是这样的:左手扶骨甲抵顶于胸腹,右手持器刻写之。倘若如此,到底是横写方便还是纵写方便?当然是纵向书写!这样才可以施加一层力保证骨甲不左右移动更利于书写,横向刻写则有不稳定之虞(因为固定“纸张”的力来自手与腹的纵向)。话题扯远了。不再考究。时来有人附会说,中国人写字阅读总是从上到下,意味着盲从和温顺,是没有反抗精神对上层建筑的礼教俯首帖耳的表现。这纯粹是哗众取宠的无稽之谈。说到底,以横画为突出特征的汉字形态及其纵向书写形式和中国建筑中的大屋顶有着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耀目夺人的标志之实证。建筑中故意把大屋顶造成曲面形,同样地,书法中这个“勒”也不能写得笔直。否则就失去了任何意义上的美感。中国文评有句话叫“文似看山不喜平”,书法也是一样的道理,“勒”画是汉字书法中最重要的笔画,是看似简单实则最为重要的一笔。“勒”画一定要避免僵直,要产生如建筑屋顶的“曲面形”,当然不是任意为之想怎么写就怎么写的。据此历代书论有很多说法。如“勒不贵卧”(张旭),“为画必勒,贵涩而迟”(唐太宗),“画如长锥界石”(张怀瓘)。禇遂良的楷书多融入隶书笔意,"勒"画长而遒媚多姿,分外醒目,通观望去却又法度尽备,器宇不凡,就是这个道理。
更要害的地方在于,横画的微微变更都将决定书字的命运,我的意思是,“勒”变则书体变。这是其他笔画所不易达到的效果。篆书只有四种笔画:横、竖、弧、圆,易圆为直易弯为折是为隶;隶书横画之“发波”似“磔”(捺脚);楷书横变较平直故书体变;行草皆使转横勒,呼应不暇,是故恣意飞舞。李邕横画整体皆取右上势,故书风险绝奇崛;板桥重墨化横为点,是为六分半书成;赵佶勒作枯枝折腋式,显瘦金体之肇端。勒之为基本笔势,正与建筑之大屋顶同。中国古代建筑对建筑群体中相似式样个体加以区别划分等级的方法就是改变屋顶的面貌。改变的方案有很多种,其样式包括:庑殿式,歇山顶,悬山顶,硬山顶,(此处大体是等级由高往低走向),此外还有卷棚顶,单坡,平顶,屯顶,拱顶,亭子还有四角、八角、圆角、盔顶等多种样式。庑殿顶四面铺张,累计五檐,八面威风。气势果然最为雄伟,相比之下,歇山顶虽然只是屋侧面的屋顶稍微向下移低了一些,就不如庑殿辉煌,而悬山只是少了两侧面的顶子,比之歇山却是相形见绌了。不过这是说气派,未必就是美感的高下。江南民居一色的白墙黑顶的悬山式样,映衬在旖旎水乡之间,分外恬美。高大威严的庑殿屋顶放在这里反倒不伦不类。从此我们可以看出中式古建筑的其他部分基本不做改变,仅仅将屋顶稍加修改,整个个风格和面貌就变了样。庄严也好,纤巧也罢,盖由此出。
所以这里提出,横画之为汉字书法的标志笔画,若同大屋顶之被看作中式建筑的象征结构。其内隐的关联,难道仅为信口之谈乎?

(四)硬与软
中国建筑结构上有个术语叫做“软性联接”,就是房屋木结构的各个构件都由榫卯联接起来,从支撑大局的柱子,到横梁,架在梁上的檩子,搭在檩上密集的椽子,而土石的墙壁只起到间隔空间的作用,并不承受多少重力,因而即便遭遇地震等不可抗力,富于韧性的结构也会支撑住整体房架,不至于倒塌。房子如此,亭台阁榭也是一样。甚至建筑内部摆设的家具,也是如此。明代的家具不用钉子,比如花梨木椅子,全是由榫结而成,且坚固耐用。这让我想到西方的文字与汉字在笔画联接上的区别,正与各自的建筑特点相似。比如英文字母。每个字词都由那几个字母硬性拼凑而成,比如同是d,g,o三个字母,这样组合就是dog(狗)再这样组合又成了god(上帝),其间毫无关联,是一种宛如拿钉子穿钉起来的硬性结构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就可以随意制造流行词汇,因为没有什么规则(当然构词法还是有一点要求的)。汉字完全不同。以书法举例,你写一个米字,你不能把一“横”下面的两笔与上面的两笔对调。把米字的横画左上的一点写成右下的一捺,或者把左下的一长撇写成右上的一短撇。字当然还能够认得出来(就象“墙倒屋不塌”一样),只是感觉上说不出来的别扭,整个字可能都摇摇欲坠,而形态也宛如一个人的双腿长在肩膀上。丧失美感和独特的结字方法。中国古建筑的软性联接是需要高超技巧的,书法也同此理,所以很多汉字的字型结构在书法中逐渐被历代书家寻找到了最佳表现的模式的形体,那些起到示范作用的书法作品也就被称为“法书”。现代汉字的简化改革,使得许多原来的繁体字面目全非,就象去掉了楼阁的大屋顶而一律造成平房一样。以至前段时间媒体也公开呼吁建设有自己特色的中国城市,因为坐火车从南到北从东到西所见的城市都有千篇一律之感。其实,千篇一律是小事,问题是书法家一时还找不到经过变形手术的汉字的最合适的写法,以至仍然习惯于书写繁体。因为这需要较为漫长的过程,去摸索怎样的“软性联接”才能够最完美地表达出那些简化字的形体美。(有些激进派人物比如王文元老先生干脆呼吁取消简化字重取繁体字,认为简化字大多根本毫无美感可言)我觉得简化字也还是有可能找出美的规律来的,只不过,这需要时间。就象现代中国的建筑师们还在苦苦求索表现中国风格的建筑作品一样。然而必须有人去做。
正所谓“路漫漫其修远兮”,老祖宗留给我们的东西,能够懂得珍惜已经不错,何况本来就已所剩无多。

(五)结构,还是结构
书法与建筑,最紧密结合处当在结构问题上。人无骨不立,书无骨不存,建筑首须建立起间架。这些说的都是结构。间架结构,在书法中谓之“结体”。赵宦光《寒山帚谈》云:“能结构不能用笔,犹得成体;若但知用笔,不知结构,全不成形矣。”,“古人不畏无笔势,而畏无结构”,又云,“用笔有不学而能者矣,亦有困学而不能者矣;至若结构,不学必不能,学必能之。能解乎此,未有不知书者。”
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说的正是建筑的结构问题。建筑要考虑到实用性,因而尤以结构端正严谨为要务。书法虽然有行草者,可以汪洋恣肆,疏影横斜,然而倘若把这看成是任意为之胡乱涂抹那就大错特错了。实际上,正如早有人反复说过的那样,怀素,张旭等大家的所谓“狂草”却是最为章法谨严,结字规矩,笔法不乱的。果真大肆涂鸦,那必然毫无审美观照可言,因为人们面对的正是一堆东倒西歪甚至支离破碎的木头与砖石堆砌一处的废墟和垃圾。
历代向有著文探究书法结构美感奥秘者。清末黄自元所著《间架结构摘要九十二法》,几乎成为后代书法教学的圭皋。其中不乏至理箴言,比如“一字无二脚”、 “画长直短撇捺宜缩,画短直长撇捺宜伸”、“横戈不厌曲”等等。我们看历代名家法书,风格各异,仪态万方。然而其结字之理相通,都遵循着普适的结构规则,未有越雷池一步者。这跟一直以来建筑基本准则的道理是一致的。在书法的结体与建筑的造型结构两者关系间,绝不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只是需要细心去对比和观照。比如“勒”字,黄氏《九十二法》中这样进行归纳:“让左者,左昂右低。”就是说,象“勒”字这种左部突出右部让步的字型,书写时要做到左部高昂伸展,右部低矮收缩。建筑中的格局也是这样。北京碧云寺有一座金刚宝座塔,在主塔旁边还有一座小塔。可谓“塔上加塔”,然而这塔不是随意加的,这样一种左高右矮(从一个侧面看)的式样设计,正呼应了书法结字中“让左者,左昂右低”的法决。有一个更微妙的例子,宁夏青铜峡有一座规模很大的喇嘛塔群,共由108座小塔构成,从山顶往下按1、3、5、7……直排到最底层的19座,形成三角形状。小塔的真实大小是越往上越大,这样就避免了透视上的误差,看上去似乎108座塔是一个大小的。与这种建筑对应的是那些字画比较茂密结构比较繁琐的字体。比如“齊”(齐)字,字画缜密繁多。《九十二法》里怎么说的呢?书云:“密者匀之”。怎样匀?黄氏范字依的是欧体,上面的一点连一横写得横贯长迈,比其他笔画要大许多,其他笔画也尽量安排匀称,造成一种视觉上的平衡感。不使上面太狭小,不使中间太逼仄,也不使底部太空阔。这与百八塔的利用透视原理何其相似!还有例子,密檐塔是佛塔非常普遍的一种形式,有个笑话说的是古代有一酸秀才学识浅薄却妄自尊大,一日赶考经过一古塔,即兴吟诗道:“远看古塔黑乎乎,上头细来下头粗。有朝一日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这里说的就是这种密檐塔。塔身基部端正粗大,塔身以上密檐部分随高度增加将每一层出檐深度都往里作不等量的递减,使塔的外型成为有弹性的抛物线形式。这样每层塔檐的起点从垂直纵轴这条线来看都恰在上一层塔檐的檐角之下。《九十二法》云:“‘彳’法,下撇之起对上撇之尾。”意思是双人旁的部首下面的撇要对齐在上面短撇的撇尖部位。说的是什么?因物象形,不正是对密檐塔构型的描述么?再来个更明显的。谈及大型的宫殿楼宇,书法有句:“天覆者,凡画皆冒于其下;地载者,有画皆托于其上。” 前者,譬如“宇”、“宫”等字,后者,譬如“上”、“盖”等字。瞻望宏伟的太和殿、天安门、乾清宫、祾恩殿,无一不是天苍苍野茫茫“屋顶似穹庐,笼盖四野”,台基则如百川汇集之阔谷“大不自多,海纳江河”。每次面对这些雄伟的建筑,我都会从心底顿时涌起万丈豪情,那感觉,就跟站在一幅雄强高迈的颜体大书前的激动一般无二。
建筑里有人性,我常常这样想,书法亦如是。

(六)借景与布白
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这个音乐怎么体现出来呢?一个音符无法构成乐曲,同理,一座建筑也很难体现出音乐性来,尤其对于中国建筑而言更是如此。
中国古建筑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就是它不以个体的独美为功用表征,相反地,中国建筑的最大特点在于靠群体生势。不论苏州园林或者北京故宫,不论佛教塔林或者北方四合院,都是以一组建筑群的有机组合产生强烈的视觉美感和功用效果。书法亦如是。一个字的书法作品不是没有,比如传统节日春节时家家户户张贴的大 “福”字,不能不说那也是书法。可是别忘了,即使是这个福字,也要有周遭的春联、横批、楣联等共同造势,形成一种浓厚的喜庆氛围。也就是说,书法在这一点上也与古代的建筑相一致,不单独地张扬单体结字之美,而是寻求一种汉字群体的组合之境。书法术语称之为“章法”,或曰“布局”、“布白”。
一篇书法作品中,布局是相当重要的一个构成部分。没有好的章法的作品甚至不可以称之为书法。古人历来对此颇为重视,唐书论家张怀瓘曾有云:“夫书,第一用笔,第二识势,第三裹束。三者兼备,然后成书。”这个识势,含义有二,一曰单字的结构关系,二就是指这个章法布局。一篇字体隽永章法优美的书法作品和好的建筑群一样,带给人的是心旷神怡的精神享受。
在一幅书法作品中,章法所要强调的是整体性。即各个单字间,线条的粗细,墨色的浓淡,水分的枯湿,笔意的勾联,结字的大小,空间的疏密,所有这一切构成一种或对比或一致或激扬或幽雅的通篇和谐的视觉感受。需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是,不光是单字,而且书法中的空白也参与艺术的表现。尤其是画面中的空白与字里行间流动的“气”,或刚健或阴柔或雄浑或恬静,这一切离不开适当留出的空白的作用。有人认为书法作品给人的感官体验和精神觉悟主要是靠笔法,而不是靠章法更不是什么空白或抽象的“气”来达到效果的。因为笔法,单个的字,就足以表现“气势”和风格了。比如颜真卿的雄强,欧阳询的冷峻,虞世南的含蓄,禇遂良的秀逸,康有为的古拙,毛泽东的豪放,林散之的旷达……都是结字和笔法的独到风格所致,哪里跟章法有关系?诚然,笔法是立书之本。一个人的笔法不精,单个字尚且写不好,哪里有什么书艺可言?而且的确,每个书家的风格主要是由其笔法,线条的表现力,结构的安排,一撇一捺的书写习惯所决定,进而形成自己独特的“书风”。人们一看到“乱石铺街”的六分半书,就知道这是郑板桥的作品;一看到“蓬头垢面”运用“涨墨”充满张力的书法,就想这是王铎的墨宝;一看到“飘若浮云,矫若惊龙”的俊逸书风,就联想到是书圣王羲之的杰作……然而再一发掘,思索,问题并不这么简单。同样单字挺拔刚劲的书法,在布局之后的表现中,可能展示出几分妩媚秀美的气息;同样绕指柔般软滑纷洒的字体却可能造成通篇淋漓尽致大气磅礴的效果。前者,譬如禇遂良的《雁塔圣教序》,看单字不能不承认每个禇体字其实都是笔力十足挺拔蓄力,然而初赏禇字的人反会感受的是秀丽典雅俊逸妩媚。以至于很多学习禇体的人过分追求其柔媚清秀结果字若无骨,绵绵欲坍。后者,譬如徐渭的《韭叶七言诗》,独观单字,缠缠绵绵,绕来绕去,毫无劲道,然全观书作,则一股汪洋恣肆,洒脱不羁之风扑面而来,让人凝神屏气无法呼吸,造成一种康德所说的“崇高”的美感。是什么造成这种反差的效果?是“气”,是章法,是空间的张力,是神思独运的布局。
建筑中讲究“天人合一”,讲究建筑与周围环境的协调,讲究景点的安排和布置。什么地方该建造凉亭,什么地方该开渠引水,什么地方矗立园景的中心建筑,什么地方开辟旷野,都要独具匠心,更要巧夺天工。这个“天工”为何?与彼同理,书法布白之“气”也。一篇书法和中国画一样,不要整篇填满,不要堵死,要懂得 “知白计黑”,一群建筑要保持活气流动的空间,切不可满眼皆建筑,谁生活在那里面会不郁闷窒息?当代建筑学有一个课题项目叫做“景观”(landscape)谋求的就是建筑周围的大场景设计与构造问题,其实就是建筑的“章法”。中国古代的建筑家们早就研究和总结过建筑方面的“章法”学问。明代万历年间的文人、造园家计成写过一本《园冶》,开卷写道:造园“虽由人作,宛自天开”。说的虽只是园林艺术,却足以说明所有建筑景观设计的机理。典型的宫城布局,北京的故宫,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在这样浩大的场地之上布置近千栋房屋宫殿,其艺术技艺所需水平之高,没有很深的造诣是决难成型的。在长达六百多米的中轴线上,一字排列天安门,午门,太和门,三大殿,两大宫,直至神武门,加上两侧的边门,蜿蜒横贯的金水河,无数的大小房屋庙宇,这样恢弘的气势,没有精心的布局,单单把每个殿堂屋宇建造好,又有何用?艺术价值大打折扣不说,整个建筑的实用性也不值一提。这就跟书法作品的全局性布白一个道理。
不光是布局问题,还有“大背景”需要考虑和分析。我说的这个“大背景”不是别的,就是指艺术范围这个大空间,即建筑的场所,书法使用的纸张。
计成说:“构园无格,借景有因”,“夫借景,林园之最要者也”。他所说的借景,就是要在建筑中善于假借当地的环境和地貌,所谓因地制宜。又说:“园林巧于因借,精在体宜”。该建亭子的地方就造亭子,该盖高楼的地方就盖高楼。他还分析了江河、湖泊、城市、乡野、山林等不同环境下建筑的不同特点和设计原则。如对于山林地最为理想,“园地惟山林最胜”;对于村庄地段,则“桃堤种柳,门楼知稼”,亦自得田野之乐;建造曲廊,要“随形而弯,依势而曲”;堆砌假山,要“宜上大下小,似有飞舞势”。可见,不同的环境对建造有不同的要求,不同的建筑物也需要不一样的环境表现。
创作书法,也跟营造园林,建筑群,是一个道理。首先要选纸,笔。徐在《笔法》中说:“欲书,当先看纸中是何诗句,言语多少,及纸色相称,以何等书,令与书体相合,或真或行或草,与纸相当。”所谓“意在笔先”,这个意,包括了下笔前的整体布局构思,包括了运笔的结字使转,包括了器具的相应选择。写行书用什么纸和笔,写小楷用什么样的纸笔,皆不可一概而论。据说王羲之写《兰亭序》使的是鼠须笔,南唐后主李煜最喜用澄心堂纸,才女薛涛设制的“薛涛笺”独有风味……写不同的字就应选不同特色的纸张笔具,以达到最佳的艺术表现力,反之亦然。在一张粗糙的麻纸上写那种爽利劲道的行书,自然很是适宜,但是写工笔楷书则未必见好;拿短锋狼毫写手卷自然得心应手,而用来书写立轴就显得力不从心,想写提匾更是“实难从命”。
总得来说,建筑也好,书法也好,刚才说的所谓的“大背景”相对“布局”而言,还是不重要的。艺术魅力显现与否的关键还是在于这个能够使“气”运行的布白上面。正因为空白可以无限“塑造”,才使它成为艺术作品成败与否的一大关键。而“空白”所以会产生这样奇妙的作用,也许正应验了心理学家荣格所谈及的“格式塔”心理学的实践意义吧!由于有空间,人们才可以自由地想象。
老子曰:“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无”,才是最高深的境界。

(七)符号与时空
有人把一切艺术的表现形式看成是符号,比如苏姗·朗格所谓的凝聚着“活的生命”的“艺术符号”,这样说来,书法当然也属于“艺术符号”之一。而且它显然比其他种类的艺术更“符号”。就有人,如林语堂,把书法看作了不起的抽象艺术符号。书法无疑是最具备“有意味的形式”的艺术品类之一。然而符号本身不足以说明问题,不足以涵盖它的一切。
什么是符号?一切可用来交流的东西。可见符号学的研究中,信息及意义是怎样产生的这个问题至为重要。而它之应用于书法艺术,也恰恰成为了缺点。忽视变化,将能指与所指分离以及排斥信息发出者和接受者的分析,这些都不利于对艺术的理解。从书法自身来讲,是一种极其精致的“艺术符号”,它的编码非常精妙,往往有天才成分,而对它的解码更有赖于对特定代码有识别能力的读者(欣赏者)。何况仅仅具备解码能力也是不够的,这里要注意书法的表情因素,每一幅作品都是有作者的“符号表情”的。根据荣格的完型心理学审美理论,书法可以说是“心理力的活的图解”。
麦克卢汉说过,媒介是一种“按摩”。那么作为传统文明媒介之一的书法,自然是通过这样一种按摩欣赏者的感官乃至心灵的方式,完成这种古老媒介的传播功能。
同样地,建筑也是一种所谓的“艺术符号”。作为歌德所谓的“凝固的音乐”,建筑已经被众多的建筑家和学者当作文化承载和传播的媒介,显示其“艺术符号”的特殊魅力。自不必再细说。
何况,所有的符号都是文化的构件,这是一个无限的指号过程。交流过程实际上是一条没有尽头的符号生产链。研究符号,我们是从能指和所指的共时性上截段分析的,而实际中这种情况是历时的,时间上是遥遥无期的。
说到时间的话题,不能不引申出中西方在时间观念上的差异。西方认为时间正是一直向前走的,过去的就不能回头,未来就展现在我们眼前。而中国人的观念其实恰恰相反:时间是条河,我们就站在河边,面对着河奔流的方向。未来从我们身后汹涌而来,现在是短暂的掠过,历史一去不可回的消失在我们眼前的远方。这从中国人对时间的词汇上就能看得出。“过去”(从我们身边流去)、“未来”(在我们身后,还没到来)。能稍微看得清的只是“现在”。庄子说的“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正是这个含义。
这和我们谈论的话题有什么关系呢?别的不说,就说书法的创作过程吧。书家信笔一挥,洋洋洒洒,从起笔到收笔,历历在目。那些写下的,再也擦之不去,就那样“一江春水向东流”,借助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我们可以知道,笔和书家与字迹的运动方向是相反相成的。当我们把书家和毛笔看作静止的时候,那么那些如河流般逝去的字体就是运动的了。正是在所有旁观者(欣赏者)的目光里,成为“过去”。从这点来说,书法不妨可以看成是一种“时间艺术”。对比西方油画,我们是知道的,油画家创作一幅作品是需要花上一些时日的,在这期间,他可以随时中止,经过数日,再重新修补。这便是西方人对时间的思维:转回头,历史就在我们身后,不妨“从头再来”。
建筑呢?当然不能从上往下盖。就象那个阿凡提的故事里讲的,在房子盖好后大喊一声:要是先盖这第三层就早完工了!这当然是笑话。虽然不从时间上去考虑中国古式建筑和书法的相通之处,以及与西方的异同之处。但是我们别忘了,建筑属于一种空间艺术。我们研究它,当然要从这里展开。
书法讲究“势”,中国古代的建筑也讲究个“势”。这个“势”,周汝昌老先生讲的好,说白了,就是“关系”。关系靠什么体现?对空间的处理。
典型的中国古代私家园林住宅里,我们看到,曲转廊回,绮窗幽户,月亮门,马头墙,各样的设计巧妙地将空间分割,调匀,处理的巧夺天工,浑然天成。因为建筑师们意识到,空间是有灵性的,是运动的,你不能堵塞阻断了它。而西方则不然,西方人以前的空间认识是空间就是空间。它就是个容器。你可以任意往里面填充它。所以直到印象派大师塞尚等人懂得了在画布中留有一定的空间,直到科学上发现物质的粒子从虚空场中冒出,在这之前,西方建筑的格局都是沉重的,丰满的,把一切都遮掩的严严实实,密不透风。走进哥特式教堂就象钻进了象牙塔,金字塔更是连根针也扎不进去,凡尔塞宫敦厚地蹲踞在那里。
书法也是这样,因为它同时也是一种空间艺术。米芾说自己一笔下去“八面出锋”,正说明书法的空间性,每个汉字在这里其实成了有灵性的有立体感的建筑。正象宗白华先生在《艺境》中对欧氏三十六条结构法解释的那样:“顶戴者,如人戴物而行,又如人高妆大髻,正看时,欲其上下皆正,使其无倾倒之形。旁看时,欲其玲珑松秀,而见结构之巧。”这种对书法字的正看与旁看,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恰好说明书法的立体特征,在一定是空间里通过笔画之 “势”的设计运转,产生对空间的微妙切割和创作。古代楼宇呼之欲出的屋檐,水边凉亭的八面通风,伫立山巅的玲珑宝塔,崇山峻岭间的吊脚阁楼……一个个在有心人的眼里,何尝不是一幅幅以时空为背景的书法杰作。
建筑与书法,都是人类以尊严的生命直接抒写的艺术结晶。说它们是符号也好,是文化的载体也好,是什么也好。“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站在这些千古年来绵延存活下来的伟大艺术品面前,我们是不是该静下心来,怀着一丝的敬意,去努力理解蕴涵其间的“遗传编码”,去参悟这份遥远的虔诚和妙思,去阅读它们无声地传播给我们的价值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