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蕉书法十讲:书病(第八讲 上篇)
在这里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书学上对于学书向来有二个不同的主张,像学诗、古文辞一样,一是主张顺下,便是依照书体的变迁入手,先学篆而隶而分而正……一是主张先学正楷,由此再上溯分、隶、篆。二者之外,也有圆通先生发表折衷的见解说:学正楷从隶书入手。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好呢?我的看法是:学诗、古文辞,顺流而下的主张是不错的、科学的;但书学方面的三种主张,似乎都是一个伟大的计划,在实际上却都是无须的。因为这几种书体,除了历史关系之外,在用笔和结体上就很不相同。学书既因实用,而以楷正为主,何必一定要大兜圈子呢?至于最后一种说法,如果学者欲求摆脱干禄、经生、馆阁一般的俗气,以及唐人过分整齐划一而来的流弊,进求气息的高洁雅驯,那么,隶、楷的消息较近,这种说法还具有二三分理由。清代有一个好古的学者,平时作书写信,概用篆书,以为作现在的楷正是不恭敬(其书札见昭代名人册牍),写给小辈或仆辈的乃用隶书,真可谓是食古不化。孙过庭云:“夫质以代兴,妍因俗易。虽书契之作,适以记言;而淳醨一迁,质文三变,驰骛沿革,物理常然。贵能古不乖时,今不同弊。所谓‘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何必易雕宫于穴处,反玉辂于椎轮者乎!”赵瓯北讥当时一辈力事复古的文学者说:“文字的起源是象形八卦。”“然则千古文章,一画足矣。”真可谓快人快语。
本人为一般的旨趣,实用为尚。因此,本讲虽标题书体,而所讲的仅限于真、行、草三种。孙过庭云:“趋变适时,行书为要,题勒方畐,真乃居先,草不兼真,殆于专谨,真不通草,殊非翰札。”真、行、草的关系,原为密切,草书虽非初学的急务,但就因为关系的密切来讲,不能不连带同讲。
(一) 真书
真书,便是正楷书。今人言小楷书,便是昔人所言小真书。真、正二字,异名同实,原是通用的。初学正楷书,宜从大字入手。若从小楷入手,将来写字,便恐不能大。昔人言小字可令展为方丈,这是说要写得宽绰,原因是因为一般学者的通病是为拘敛而不开展。其实大小字的用笔、气势、结构是不同的,我们看看市上所流行的《黄庭经》放大本,对比一下便可明白,小字是不能放大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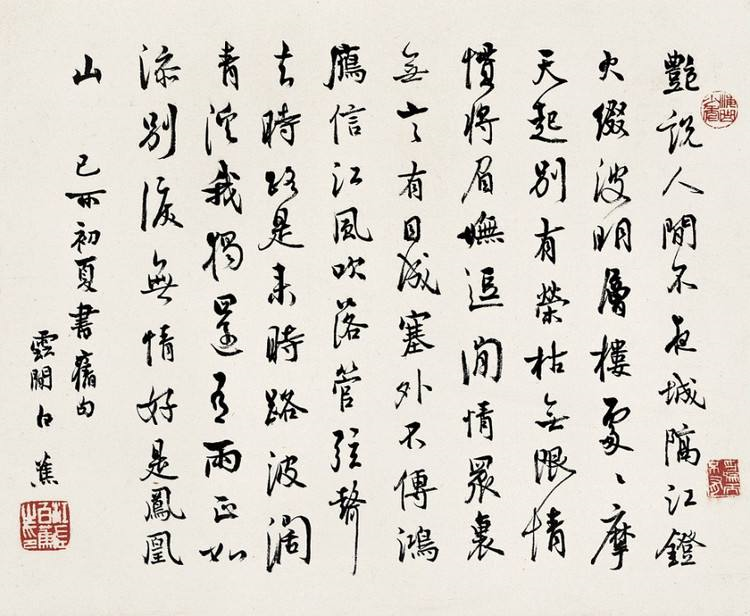
初学根基,为何先务正楷?为何正楷不容易学?古人颇有论列。
张怀瓘云:“夫学草行分不一二,天下老幼,悉习真书,而罕能至,其最难也。”
张敬玄云:“初学书,先学真书,此不失节也。若不先学真书,便学纵体为宗主,后却学正体,难成矣。”
欧阳修云:“善为书者,以真楷为难,而真楷又以小字为难。”
蔡君谟云:“古之善书者,必先楷法,渐而至于行草,亦不离楷正。”
苏东坡云:“真书难于飘扬,草书难于凝重。大字难于结密而无间,小字难于宽绰而有余。”又曰:“真生行,行生草;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而能行,未能行而能走者也。”又曰:“书法备于正书,溢而为行、草。未能正书而能行草,犹未能庄语而辄放言,无足道也。”
宋高宗云:“前人多能正书而后草书,盖二法不可不兼。正则端雅庄重,结密得体,若大臣冠创,俨立廊庙。草则腾蛟起凤,振迅笔力,颖脱豪举,终不失真。所以钟、王辈皆以此荣名,不可不务也。”又云:“士于书法,必先学正书者,以八法皆备,不相附丽。至侧字亦可正读,不渝本体,盖隶之余风。若楷法既到,则肆笔行、草间,自然于二法臻极,焕手妙体,了无阙轶。反是,则流于尘俗,不入识者指目矣。”
曹勋云:“学书之法,先须楷法严正。”
黄希先云:“学书先务正楷,端正匀停,而后破体。”
欲工行、草,先工正楷,自是不易之道。因为行、草用笔,源出于楷正。唐代以草书得名的张旭,他的正书《郎官石柱记》,精深拔俗,正是一个好例。学真书,本人主张由隋唐人入手,其理由已在第一讲谈过。但唐人学书,过于论法度,其弊易流于俗。而初学书,又不能不从规矩入。那末,于得失之处,学者不可不知。兹节录姜白石论书:
“唐人以书判取士,而士大夫字书,类有科举习气,颜鲁公作《干禄字书》是其证也。矧欧、虞、颜、柳前后相望,故唐人下笔,应规入矩,无复魏、晋飘逸之气。”
“真书以平正为善,此世俗之论,唐人之失也。古今真书之神妙,无出钟元常,其次则王逸少。今观二家书,皆潇洒纵横,何拘平正?”
“字之长短、大小、斜正、疏密,天然不齐,孰能一之?谓如‘东’字之长,‘西’字之短,‘口’字之小,‘体’字之大,‘朋’字之斜,‘党’字之正,‘千’字之疏,‘万’字之密,画多者宜瘦,少者宜肥,魏、晋书法之高,良由各尽字之真态,不以私意参之耳。”
姜白石这些话,并不是高论,而是学真书的最高境界。眼高手低的清代包慎伯,他是舌灿莲花的书评家。所论有极精妙处,也颇有玄谈。他论《十三行》章法:“似祖携小孙行长巷中。”甚为妙喻。元代赵松雪的书法,功力极深,不愧为一代名家,其影响直到明代末年。推崇他的人,说他突过唐、宋,直接晋人。但他的最大短处,是过于平顺而熟而俗,绝无俊逸之气。又如明代人的小楷,不能说它不精,可是没有逸韵。
我国的书法,衰于赵、董,坏于馆阁。查考它的病原,总是囿于一个“法”字,所以,结果是忸怩局促,无地自容。右军云:“平直相似,状如算子,上下方整,前后齐平,便不是书,但得点画耳。”学者由规矩入手,必须留意体势和气息,此等议论,不可不加注意。学者的先务真书,我常将此比之作诗作文,有才气的,在先必务为恣肆,但恣肆的结果,总是犯规越矩,故又必须能入规矩法度。既经规矩和法度的陶铸,而后来的恣肆,学力已到,方是真才。同样,画家作没骨花卉,必须由双勾出身,然后落笔,胸有成竹,其轮廓部位超乎象外,得其神采,得其圜中。孙过庭云:“若思通楷则,少不如老;学成规矩,老不如少。思则老而逾妙,学乃少而可勉。勉之不已,抑有三时,时然一变,极其分矣。至如初学分布,但求平正;既知平正,务追险绝;既能险绝,复归平正。初谓未及,中则过之,后乃通会。通会之际,人书俱老。仲尼云:‘五十知命也,七十从心。’故以达夷险之情,体权变之道,亦犹谋而后动,动不失宜,时然后言,言必中理矣。”学成规矩,老不如少,初学于正楷没有功夫,便是根基没有打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