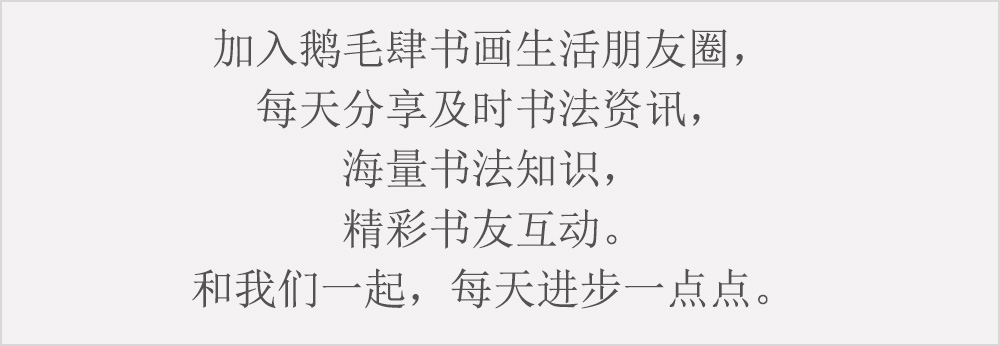中国书画何以推崇“古”?

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具有一种尊“古”的风气,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也有一种崇“古”的倾向。东汉的王充曾对这一风气和倾向进行了质疑和批评。他的质疑和批评是在“古今”视野中展开的,反对“珍古而不贵今”,“好高古而下今”。20世纪初,“五四新文化运动”也对以“古”为标志的各种文化传统形态展开了猛烈的抨击。这种抨击虽以“古今”框架表现出来,但其内涵却是“中西”问题,即以“西”贬“中”,以“西”代“中”,以先进的、强盛的西方文化和艺术来否定及取代古老的、陈腐的中国文化和艺术—然而这都恰恰反过来表明,以“古”为尚的中国传统文化和艺术具有一种连绵不绝的历史涵量和内在的魅力在古今更迭和交错的时空中曾引发了人们多么强烈的反应。在我看来,中国传统的书画艺术以及思想文化之所以尊古崇古,主要是出于如下几个原由:

一、“古”往往呈现出一种完备的格局和体系。庄子在《天下》篇中说,古人“道术”,“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六通四辟,大小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并且“《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春秋》以道名分”,其格局和体系都已然十分完备(“古之人其备乎!”)。同样,唐人张彦远认为,绘画在经过“上古”“中古”的积累和培育,演进至盛唐已然达到“焕烂而求备”的程度。宋人苏轼也认为:“君子之于学,百工之于技,自三代历汉至唐而备矣。”例如:“诗至于杜子美,文至于韩退之,画至于吴道子,天下之能事毕矣。”其实这种格局的完备并不意味着万事已“毕”,并不意味着事物的终结。文化艺术仍在且仍可发展,然而这种发展却只能是对“古”的分述,按照庄子的说法,叫做“其数散于天下”,“称而道之”,“各为其所欲”,“以自为方”。

二、“古”往往代表了一种纯正的法度。“法”在先秦思想家那里仍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如荀子和韩非子),到了六朝则转化为一个艺术学概念。谢赫提出的“六法”就是对绘画创作“法度”最早、最精当的概括。从六朝直至隋唐的书法家则对书法用笔和结体的“法度”做出了深刻总结。应当说,这些从书画实践中提炼和确立起来的“法度”不仅是书画创造必须遵守的基本规范,而且也成为书画审美智慧的象征和凝结。唐宋以来的书画理论关于“古法”的说法多得不得了。唐人张怀瓘的书法论著中就有“古法”“体法”“百代之法式”“万世不易之法式”等说法。宋人沈括说:“古法”“律度备全”,学书“须自此入”,“过此一路,乃涉妙境”。宋人董逌说“书贵得法”,要“于法可据”,“不合于法者,亦终不可语书也”。明人董其昌也一再强调,绘画应当“酝酿古法”“动合古法”。明人谢肇淛同样强调说,绘画“必欲诣境造极,非师古不得也”。尽管有不少书画家声称要“变法”,这样的言论也多得不得了,但无可回避的是,这些“古法”却是他们进入书画“妙境”的第一道门槛,也是他们书画欲达“诣境造极”的关键一环。这是因为这些凝缩了古人审美智慧的“法度”乃为感合自然万象的创造结晶,也是酝酿千年、千锤百炼、百世难易的经典样式,集聚和散发出了一种惨淡经营的纯正品质光辉,从而从根本上规范着中国书画健康发展的主航向。正如清人王时敏所言:“画虽一艺,古人于此冥心搜讨,惨淡经营,必功参造化,思接混茫,乃能垂千秋而昭后学。”因而就是注重变法的陈洪绶也都严斥“不师古人”“挥笔作画”的倾向,进而感叹说:“古人祖述之法,无不严谨。”只有“死心观之”“学之”,才能“中兴画学,拭目俟之”。

三、“古”往往体现了一种较高的格调和境界。老子、庄子和荀子的论著中有大量“古之所谓”“古之为”“古之”等说法。这些说法就预设并寓含着某种高悬在上的意味。这是根植于古代思想家精神世界中的原始“情结”。中国传统书画理论中有所谓“古意”“古趣”“古格”“古淡”“古色”“高古”“僻古”“沈古”“浑古”种种说法,则是进一步将“古”预设和构想为某种较高的格调和境界。书画家仿古、摹古、师古,与古人血脉贯通,使古人神韵自然凑泊笔下,进而以我之性情合古人之性情,一方面固然是为了把握古人的规范和法度,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只有接近古人才能使自身的创造趋于和保持着一种较高的格调和境界。宋人刘正夫说:“观古之字,如观古鼎。学古人字期于必到,若至妙处,如会于道,则无愧于古矣。”这里所谓“古鼎”“会道”之“妙”,正是对“古”所蕴含的较高的格调和境界的赞誉。清人王时敏评述赵孟頫时说:“于古法中,以高华工丽,为元画之冠。”又评王石谷:“罗古人于尺幅,萃众美于笔下。”这表明赵、王二人正是从“古人”“古法”中获得“高华工丽”“众美集萃”的格调和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