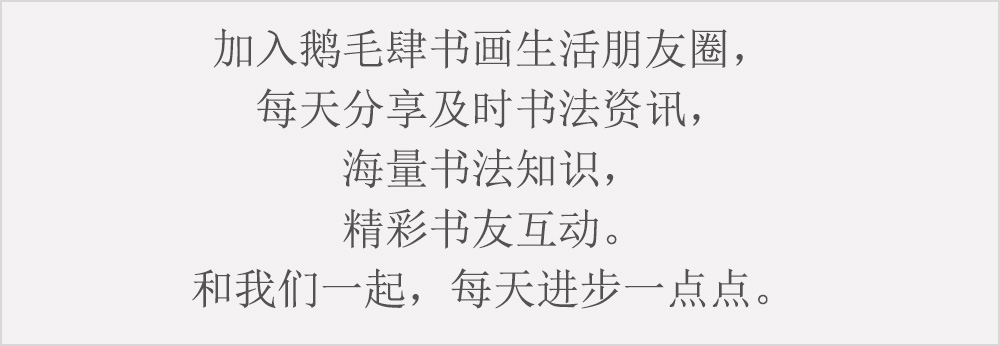他是南唐贾宝玉,中国最会写词的忧郁皇帝
壹
他是个双面情圣王
李煜接手南唐时,掌中山河早已成了破败草堂。
可倒霉的是,这文弱皇帝性懦弱,善掩藏。旧日里,为了避免兄长暗中“出老千”,他光顾着装瞎了,压根没认真学什么从君为政之道啊!
事已至此,干脆就安耽点,当个亡国小昏君得了。

李煜呢,偏偏不肯。他广施善,修庙宇,恋奢荣,撩妹子。摆出一副“感天动地有情郎”的模样。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钗袜步香阶,手提金镂鞋。画堂南畔见,一晌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有传,这阙词是李煜写给小周后的。彼时大周后娥皇病重,其妹入宫照看。
没多久,李煜与这位“警敏有才思,神采娴静”的小娘子看对了眼儿。两人一步错,步步错。
碍于夫妻情分,出于皇帝颜面,李煜并未即刻纳妃。然纸难包火,娥皇得知了双重背叛,竟日渐病重,不治身亡。
此时的李煜,碎了心。
若是常人,恐怕早就享受那新欢在卧的小日子了。这南唐后主却为此瘦脱形,连缓行几步都需持杖。
伤怀时,他曾自称“鳏夫煜”。还写了篇老长老长的悼亡文:
“昔我新昏,燕尔情好。媒无劳辞,筮无违报……执子之手,与子偕老。今也如何,不终往告。呜呼哀哉!”(《昭惠周后诔》)
爱情中的李煜,是典型的矛盾综合体。“得不到永远在骚动”的人之劣性,在他身上展露无遗。
因为情切,他注定会偷;也因意深,他只能选偷。
你说他和娥皇故剑情深,他偏偏出了轨,偷了小姨子;说他薄情似蒲苇,他却来个五年生死两茫茫。
想得却不可得,你奈人生何。
三年后,李煜迎娶小周后。她成婚那日,一如姐姐当年身着红罗长裙,恰也芳龄十九。

贰
他活在鸵鸟世界里
抛开爱情。
生活中的李煜,亦是个逃避型人格患者。
自幼时,他就长于妇人之手。双鱼座心性,十足小文青一个。身为家中老六,他上位的几率极小,无异于帝都摇个车牌号。
不凑巧,李煜偏生着一张帝王脸,“广额丰颊,骈齿,一目重瞳子”。为防哥哥们算计,他干脆当个认怂主义者。
这边跑个钓鱼俱乐部,那边入个佛学协会。偶尔呢,也当个书画院院长、混个妇女协会之友。
然而,生活总是不乏狗血。越是逃避问题,就越被问题死缠。
李煜那五个老大哥,都命薄。先后翘了辫子。小六儿丛嘉,竟然从最初的持外卡冷板凳,一跃成为头号种子选手。
两年后,李璟死。金陵城中,新主代旧皇。此时的李煜,在阑珊梦中一晌贪欢,在亡国路上欲走愈远。

有野史载。宋太祖提及后事,曾笑谈,“若以作词功夫治理国家,岂为吾所俘也。”
我以为,这话有点因果倒置。李煜痴迷诗文,除却兴趣使然,自有“逃避”的成分。
国家系危难存亡之秋,他自杀没勇气,苟活不自在。个人价值感的唯一来源,唯有手中纸笔而已。
生在帝王家,却无帝王心。承不住一国之君的责任和担当,却贪恋万人之上的奢荣和声色。
这本来就是悲哀。
不过呢。被惹恼的李煜,也会“撸起袖子当爷们”。
可帅不过三秒。袖子刚撩一半,赵匡胤的“宋军敢死队”已攻破长江天险,一路开外挂般杀到金陵城下。
此时,李后主逃避型人格中另一特点暴露——偏执,不听劝。
忠将林仁肇,看不下这番惨状。曾恳请带精兵几万,收复江北失地。
只恨那时,李煜已罔顾他人之语。惶恐中,他无视宋军的反间奸计,生生毒死了身边大将。
“一旦归为臣虏,沈腰潘鬓消磨。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
骨子里的懦弱心性,使李煜无力支撑这残局。不出几日。他带领一众群臣家眷,裸着上身出城——“肉袒降于军门”。
想想也是可悲。活了半辈子,几曾识干戈。
当南唐后主甘心扮演弱者、奴隶、胆小鬼之际,其敌手自然就成了强者、暴君、刽子手。

叁
他有颗天真少年心
又是几年。赵匡胤挂了,大宋王朝董事会发生剧变。赵光义掌权,一举成了CEO。
彼时,李煜的好日子真正到了头。
“多少恨,昨夜梦魂中。还似旧时游上苑。车如流水马如龙。花月正春风。”
可怜那小周后,被三番五次接入赵光义的宫闱。每每爱妻返家,俩人相顾无言,惟有抱头饮泣。
李煜心里太窝火。既已成了阶下囚,本该收敛的。偏偏他牢骚满地,宁做宫中一愤青。
“多少泪,断脸复横颐 。心事莫将和泪说,凤笙休向泪时吹,肠断更无疑 。”
“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 ,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
天真如后主,都死到临头了,依然傻的可以。
他错把诗词当树洞,错将异地视他乡。那自以为管用的“诗词止疼药”,一片片,成了赵光义的眼中钉、心头恨。
周之琦曾在《词评》中评价,“予谓重光天籁也,恐非人力所及。”
想来也是,李煜虽已中年,却仍是少年脾气。那星点的软弱与怯懦,无不以感性来直感。
他把自己活成了普通人。却终究性情了些。
某日午后。旧臣徐铉前来拜访。后主像小孩子见着亲妈,生生忘了自己是被软禁的囚犯。
“当时悔杀了潘佑、李平!”实诚如后主,拉着徐铉之手,一哭二嚎,诉说当年斩杀忠将的悔意。
谁曾想。徐铉是探子,转身即告密。宋太祖一听,原地爆炸。他本就视李煜为情敌,横竖都不爽。
这下可好,揪到了“意欲谋反”的小辫子,岂不杀之而后快?更何况了,那首“春花秋月何时了”,反宋反百姓,越瞅越像毒草。
果不其然。太平兴国三年,七月七。李煜被赐一壶寿酒,身中牵机毒。惨死于汴京。
未多久,小周后哀不自胜,亦辞世。
“世事漫随流水,算来一梦浮生。醉乡路稳宜频到,此外不堪行。”
千年后,群众们吃瓜。叹李后主荒淫误国,讽他阶下囚、违命侯。然而,在千年前尔虞我诈的宫墙之内,有多少事由不得人?
世人讽他太薄情,喜新而厌久,却忘了他十几年如一日对娥皇的笃爱和歉意;
世人怨他性骄奢,不恤国情,却忘了他离恨也似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这一生。终究是矛盾而戚然的。
如王国维所言,“后主之词,真所谓以血书者也。” 最美好的东西,惟以最沉痛的代价来换。
不曾忘。那时李煜字重光、初名从嘉。从嘉从嘉,意为“一切皆好”。
我自当他是少年郎。爱情可成诗,心事可成词,悲意可谱曲,饮鸩亦成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