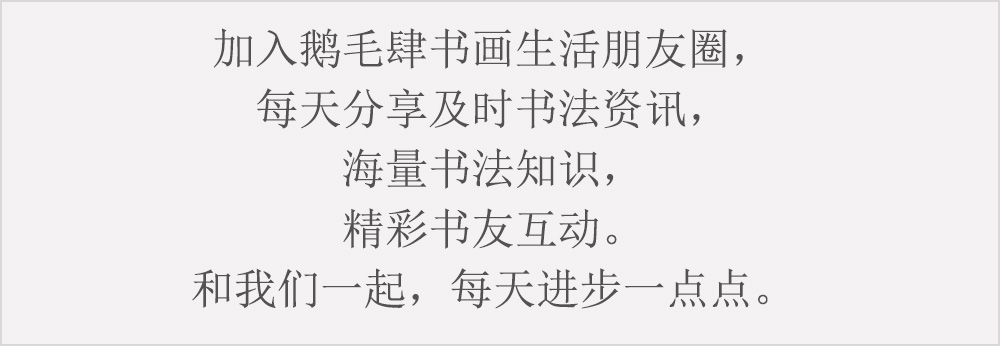《书法报》精读 | “计白当黑”内涵的拓展
2017-06-20 11:04:14 来源: 点击:
文 嵇绍玉
“计白当黑”源出自《老子·第二十八章》“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学者任继愈先生翻译为:虽深知他的光彩,却安于他的暗昧,甘作天下的车 轼。衍生到哲学领域,就指要知阳守阴、知刚守柔,则可成为天下的楷模样式。延伸到书法艺术,最通俗的解释为,在书画艺术中要注意用空白之处,来表现笔墨已到或想到之处,空白之处也是章法和意境整体所在,它与笔墨之处存在相互依存、合而为一的关系。因为空白之处,是笔墨蓄势待发或补遗增益的巨大空间,不仅是笔墨之处的依附所在,同时也是与之相互生发、互为补充的必要前提。当书家取诸怀抱,付诸笔墨时,作品一方面在创造可观的有形有限之象,另一方面也在创造字形物象背后可感的广博世界,而这世界有赖于笔墨之处与空白之处两者交融共同提供。如果从艺术哲学的高度来进一步分析,“白”生“黑”,“黑”生“白”,“白”可当“黑”,其本质内涵实际上还要丰厚得多,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含义。
一、计简以当繁
文字的肇始,因要象形和表意,非常繁复,但在经过约定俗成和融会贯通的阶段,人们已经熟悉认同后,对其简省变革便提到重要日程。.从篆到隶到行,走的就是一条简省线路。特别是汉草的应运而生,把简省推到极致。作为汉草,对其先前的书法传承和创新,主要特征就是“一省二简三连”。省略字的笔画和部件,简化结构,以简单的结构来代替繁复的结构,并把本来应该逐笔书写的点画连贯起来,写成一笔,并使得这一笔生发出干变万化的无尽之意。应该看到,追求简省,固然出于便捷的需要,但实质上也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求简求省的普世情怀。《老子》中说“为学之道,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无为而无不为”。之所以要“损”,因“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而道之“损”,则从主观到客观、从理想到现实、从特质到精神,把由生活通向理想的百阻干隔、重障叠碍,一一加以损掉,实现生存状态的最优化。减之又减,约而再约,在这简省的过程中,事物的本来面目就会展示出新的广阔空间。一方面简省的是多余累赘的构建,简省了负担和分散视力的东西;另一方面简省的是不当审美追求和笔墨技巧。执繁控多,本是艺术创造的大忌,清书画家恽南田在他的《南田画跋》中说:“妙在平澹,而奇不能过也;妙在浅近,而远不能过也;妙在一水一石,而干崖万壑不能过也;妙在一笔,而众家服习不能过也。”这足以说明简省的必然和必要。在书法滥觞期,先贤们并没有掌握多少书法技巧性能,实用的需求远远大于艺术的美感,用笔还‘没有可能分蘖(nie出那么多的中锋、偏锋、提按快慢的概念,随着书体的衍变,五体俱全,审美意识自觉自醒,相应于五体的各类技巧才应运而生。任何艺术技巧都有其从发生到成熟的过程,一种成熟的技法总会趋于固定趋于保守,技法的成熟便开始束缚和消磨着艺术家文化创新的力量。当人们意识到这一点时,便发现原先的技巧太复杂,难以辨别,徒炫耳目的所谓技法委实不少,于是便开始去伪求真剔除那些华而无用的所谓技巧。值得注意的是,“简”不单单是就“简”,而是为了当“繁”。不能越简单而越简单,而要越简单越丰富,越简单而越洞幽烛明、拔茅连茹。书法不过是点线的组合,它没有绘画、音乐、建筑那样的丰富性,然而,在某种意义上,书法却比其他艺术在主体上更需要技的训练和文化底蕴的积淀,因为书法仅依靠赤裸的线条支撑着人们可兴寄、可言志、可抒情的重大功这线条如果简单得不足以深深拨动欣赏者的心弦,不能承受着巨大的艺术感染力,这“简省”的线条就毫无意义、毫无价值。“计白当黑”的本质,就在于让欣赏者从简洁的线条中透视出最大的蕴涵和无尽的信息量。
二、计藏以当露
书法线条的“藏”是线条书写的技巧。所谓“藏”或所谓笔画“藏头护尾”,是指笔画在起笔与收笔过程中要“逆锋”,使笔锋不外露。古人说:意有不可直言者,不得不曲。唐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说:“似往已回,如幽匪藏。水理漩湫,鹏风翱翔。道不自器,与之圆方。”诗和书法在表现上一样,书法线条中意有不可直露者,不得不“藏”。唐韩方明《授笔要说》中说:“夫执笔在乎便稳,用笔在乎轻健,故轻则须沉,便则须涩,谓藏锋也。不涩则险劲之状无由而生也,太流则便成浮滑,浮滑则是为俗也。”这就揭示了用笔如果从相反的方向来运行,力量则雄强饱满,这也正是《老子》所说“反者道之动”的意蕴所在。为此,宋代米芾才提出“无垂不缩,无往不收”这一“八字真言”。秦李斯篆书中的线条特别注重“藏头护尾”“内含筋骨”“力在字中”,使得作品表现出含蓄蕴藉之势。魏碑中多藏锋落笔折而成方形,线条棱角分明呈现出骏利之美,又表现出融合流动之韵。唐颜真卿的楷书常以藏锋入笔顿以圆形如锥画沙,表现出雄浑厚重的风格。相反,也有的书法家惟恐作品传递的信号太弱,创作中总着眼于线条的露、张,而忽视其“藏”的效果。诚然,书法线条中的横竖撇捺都是作者可以信手发挥的,让作者极力张扬成为可能,使得他们在创作中时而笔力圭角分明,时而顺势直下,以为轻盈浮滑,便可增大信息的传递量。其实,正如清梁巘《评书帖》所说:“(张瑞图)书得执笔法,用力劲健,然一意横撑,少含蓄静穆之意,其品不贵。”意指张的用笔,少含蓄敛藏,作品信息传递反而微弱,品质不贵。
三、计静以当动
“静”与“动”,从哲学角度看,是一对矛盾,而正是这对矛盾的运用,才赋予平面上的书法以生机,使其生动活泼昂然起来。不错,书法艺术通篇是“静”的一维艺术,犹如安详之水潭,如果通篇是活动的字,那它就是立体的艺术、动态的艺术、机械原理的艺术。书法艺术所讲的“动”主要指书者创作时的“运动”,书法作品的“动感”以及观赏者心灵之“震动”,都是凭“静”来实现的,无“静”就无所说的“动”。
书法之美,实质就是造型运动之美,而不是静止不动的点状之美。但这种运动之美,来源于书家心灵的安静、默然、凝思和集虑,唯这样的运动勾画出来的点画结构章法才是成熟的、卓著的。就“动感”来说,同样是“静”的存在,才有动感产生的可能。我们知道,篆书、隶书和草书“计静以当动”比楷书更强烈一些,因为其线条和形体变化张翕较大。至于书法作品给观赏者以心灵的震动,那是书法审美中更高层次的追求,优秀的作品都具有这样的资质。唐孙过庭在《书谱》中说:“好异尚奇之士,玩体势之多方;穷微测妙之夫,得推移之奥赜。著述者假其糟粕,藻鉴者挹其菁华,固义理之会归,信.贤达之兼善者矣。存精寓赏,岂徒然欤?”说的就是书者和观赏者与文字之间心灵的沟通默契。曾说过“常计白以当黑,奇趣乃出”的邓石如,就深谙其道,他的《庐山草堂记》,给人一种清秀洒脱、浑厚的感觉,让观赏者叹为观止。
四、计方寸以当万象
古人云:“咫尺之内,便觉万里为遥。”西汉扬雄《法言·问神》中说:“弥纶天下之事,记久明远,着古昔之昏昏,传千里之忞(min)态者,莫如书。”唐韩愈《送高闲上人序》中说:“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意即奇纵舒展而笔势豪健的狂草,不仅可以抒发自己的情感,同时也暗示自然客体种种变动万千的审美意象。书作通过本体的暗示、隐喻、联想或比拟式移情,将大干世界万种风情在书作中一一加以展现。
那么书作方寸之间,何以展示万象世界?究其原因,主要得益于其丰富的想象性。《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儒家的“吾道一以贯之”的哲理,构成了书法“计方寸以当万象”的理想基石。书法从方寸之间的一条线一个结体开始,繁衍演化为难以尽计的形、质、势、法,完成不可计量的书艺杰构,主要依靠想象来完成。观赏者通过想象才生发出人心之美,生发出万象之美。汉蔡邕《书论》:“纵横有万象者,方得谓之书。”
想象性之外,还得益于其抽象性。方寸之间大都是较抽象的,唯其抽象,才能容纳得下无限的外延。唐张怀瑾在《书议》中说:“囊括万殊,裁成一相。”万殊之象,可用一笔来囊括之,因为万物之象,有其美的构成的共同之事理,抽象出这事理,便可以反过来还原出万物来;笔墨方寸之间才又还原出其书作背后的实物形象和诗情画意。同时,也得益于其模糊性。书法艺术可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形象”“意象”无法用精确逻辑的方法加以具体地描述,而只能以模糊来论述之。模糊而不确定,带有一定的游移变动发散性质,才会让书家和观赏者有所补益,抒发出情感,才体验出艺术的本质力量。晋卫夫人《笔阵图》说书写的点画“隐隐然其实有形”,因点画之模糊而让观赏者产生联想和想象,有着实物的存在。模糊性可以说是所有艺术的共性,但它又有内在的必然性。蔡邕《笔论》中说,创作时“凡欲结构字体,皆须象其一物”,书法艺术的特质,决定其不能模糊到无规无则、无象无形,而要有相应于现实事物的形象和意象之存在,这与书法艺术源自象形为主的汉字有关。
五、计空灵以当充实
《老子》“无”的哲理,洗涤了芸芸众生的心灵。书法艺术也在追求空灵中,处处体现充实的存在。观赏者透过空灵,依稀看到作品中光的洒落、气的流播、神的耀显,看到生命的俯仰盘踞、手足举投和蹒跚蹁跹。而从两晋开始,外来佛教的渗入,书法演进在老庄哲学浸染下又注入一支新的催化剂。佛教“色空观”对书法美学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这几方面:一是“心定”之充实。正因为书家专志凝神,意空虑绝,才使他们创作时没有宗教背景,没有皇权旨意,没有门派之累,没有任何世俗强压在书家身上的沉重包袱。二是“融通”之充实。佛理强调要突破干仞之规矩,一言以蔽之,就是反对执著不化,僵化固守。这对书家们排斥逻辑认知,避免陷入二元论的泥淖,利用“潜心冥想”意识流淌去把握书法的真谛,并作为书法最高的审美情趣,极为有益。三是疏淡风格、平和意境之充实。史上二王书法风格就属于此类,体势流美,表现出不激不厉、萧散简淡、风规自远的审美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