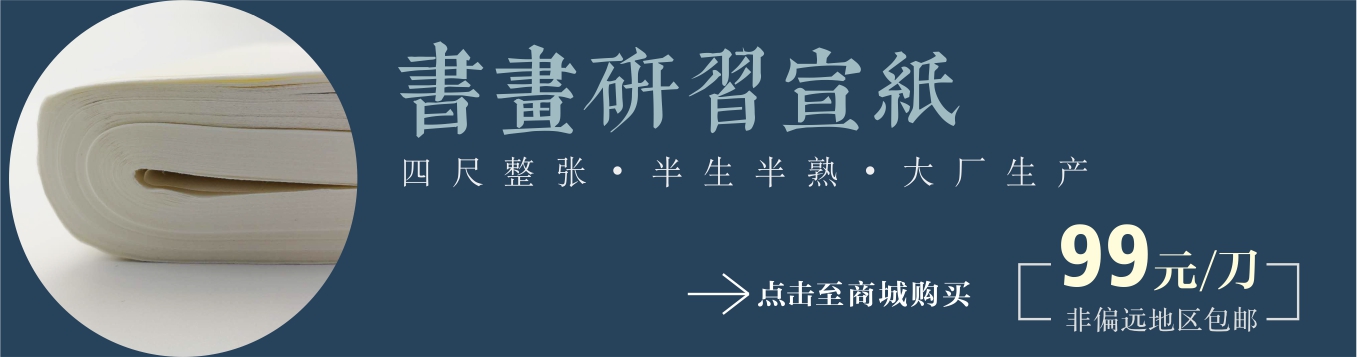《好太王碑》
2019-12-03 13:36:37 来源:网络 点击:
好太王是高句丽王朝第十九代王,全谥为国冈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碑建于公元四一四年,碑身是角砾凝灰巖,风化严重,常年剥落。『国冈上』为埋葬地点,现在吉林省集安市九华里太王公社大碑街,大型阶坛积石墓,属于高句丽国内城遗址,当时的王都。从公元三年,儒留王(琉璃王)迁都国内城起,直到好太王之世,这里一直是高句丽的政治中心。唐代贾耽的《道里记》记载这里曾是高句丽王都,是当时渤海朝贡道上的一个重要经点。

好太王碑清末民初原始面貌
王健群先生縂结:碑文内容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记述高句丽建国的由来传说,邹牟王、儒留王、大朱留王祖孙三代王位的承袭,并简述好太王的形状;第二部分,记好太王征碑丽,伐百济,救新罗,败倭寇,征东扶余等事实,以及战胜所获城池村落和生口;第三部分,是根据好太王『存时教言』,对好好太王墓守墓烟户的来源、家数作了详细记载。好太王为上祖先王墓上立碑,『铭其烟户』,并制定了对守墓烟户『不得更相转卖』的制度。目前大多数学者沿用早期研究成果,认为守墓烟户的身份是奴隶,其实应为城民(国烟)和谷民(看烟)两种的农奴,概念不一样的。
晩清时任职奉天府军粮署同知的王志修作有《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将此文作为范文向当时与试者宣读,其中有『稽古名不录欧赵,访碑近未逢孙黄。』一句来形容好太王碑的传奇存在,『欧、赵、孙、黄』都是著名金石学者,以稽古访碑著称,分别著作有《集古录》、《金石録》、《寰宇访碑录》、《小蓬莱阁金石文字》,但这些著作中都没有收录好太王碑。原因是从金代开始,高句丽故都失去记载,逐渐被世人遗忘。清代康熙年间,为了保护满族祖先的发祥地,将长白山一带划为封禁之地,任何人不得越边到这里垦殖,违者重罚,使得这一带更加荒僻。直到光绪初年,公元一八七五年前后,才被中国少数金石学家所发现并讨论研究,明确了这块巨大石刻是高句丽广开土王墓碑。

顾燮光的《梦碧簃石言》书影
清末金石学家顾燮光的《梦碧簃石言》里记载了,他朋友戴奎甫告诉他是光绪元年发现此碑,戴奎甫曾到集安查学,在开荒东边荒地时发现此碑。《辽东文献征略》里有一篇重要文献——谈国桓的札记,谈国桓曾任清末任奉天(沈阳)税捐总局局长,他说他得到一张好太王碑的拓本,这个拓本是怎么来的呢?一个朋友送给他的,这个人叫关月山,资料不多,当时怀仁县设治委员叫章樾,关月山是章樾的幕僚,喜好金石,可以自行拓碑,公余之暇寻访古迹,便发现了好太王碑,不过『获此碑于荒烟蔓草中』,碑石上全是苔藓,仅手拓数字。谈国桓说当时并没看到全本拓本,因为『以碑高二丈余,宽六尺强,非筑层台不能从事,而风日之下,更不易措手也。』这次记载非常珍贵,不仅记录了最早发现的时间,具体情况也很清晰,第一次公布了石碑的尺寸,记录下了好太王碑最初的拓本版本,这也是数字拓本的面世,轰动了金石界。章樾从关月山处得知好太王碑的情况后,下令清除碑面上的苔藓,这时开始出现第一批拓碑的拓工,王志修(令下属传拓)、李大龙(京师碑贾,善拓,也有记载名为李云从。)、初天富(职业拓工,后人继承拓碑工作至一九四九年后。)谈国桓札记里还写到谈国桓的父亲谈广庆,受人所托,在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以后,曾两次派人到桓仁拓碑,得拓本六本。谈家藏有自拓光绪十三年精装拓本。这时拓本的完整度和尺寸开始扩大,不过烧苔藓时,因为火旺而使碑石出现裂隙,并崩裂小块碑石。

一九二七年集安工商各界集資修建好太王碑碑亭
李大龙是碑贾,远途拓碑一定有利可图,他的雇主就是京师最早得到碑拓的潘祖荫,据说带着粮食在集安住了很长时间,『历尽艰险得五十本』(张延厚跋语,张祖翼之子 )。潘祖荫亲自研究以外,还委托叶昌炽进行考释,此时的拓本都是散页,拓工没有辨识能力,顺序混乱,字迹模糊,拓工还进行了描摹处理,即双勾添墨拓本。吴大澂收藏的拓本也是同类,是从陈士芸手中获得(见《皇华纪程》)。罗振玉的《俑庐日札》和《满洲金石志》序中都有李大龙拓碑的记载。遗憾的是李大龙二度前往拓碑不久后,潘祖荫便逝世,这位藏拓第一人并未成为第一位发表研究成果的学者。

一九二八年好太碑碑亭建成,一九七六年秋,碑亭拆除
王志修除了之前提到的《高句丽永乐太王古碑歌》,同时还写了《高句丽永乐太王碑考》,是一部实地考察的详实著作。在王之前,还有丁少山曾进行考证,但未完成文章,所以王志修的这两篇详实的文章成为最早的研究成果。可惜他生逢乱世,文章只在当地传播,又官属末品,故不为人所知。王志修将自己的文章给他的一位同族长辈王懿荣看过,王懿荣是金石学家,收藏有好太王碑墓砖,王懿荣又将这两篇文章给郑文焯看过,郑文焯开始关注好太王碑便是这时开始的。郑文焯自述也得到好太王碑拓本,我藏有一册郑文焯着《高丽国永乐太王碑释文纂考》,光绪二十六年经注经斋刊行,费资刊行可见当时对此作的重视。虽然郑氏考证的结论现在大都有新证,但因郑文焯深通音韵词章,有他独到的关注点,他认为好太王碑文『铭词无均(韵),文义简絜疏宕,叙事处有类范史之笔』,从文学家角度作出了评价,推崇为辽东第一古碑。我还见过郑文焯题跋的好太王碑墓砖拓本,不下五份,都是数次考释题跋,足见其对好太王的关注和喜爱。

罗振玉像
而对好太王碑带来的史实价値,考证最有贡献是陆心源和罗振玉。陆心源并没有专著刊行,只有题跋文字流传,跋文主要对比《后汉书·东夷传》、《三国志》注中所引《魏略》、《魏书》、《隋书》、《文献通考》、《东国通鉴》等书,考订东明建国传说。又引《三国史记》,高句丽谈德谥号广开土王,认为此碑应题为《高句丽广开土王谈德纪勋碑》,这是重要的一次考证确认,为同时人提供了更为准确的讨论信息。罗振玉关于好太王碑的考证主要收入在《俑庐日札》和《唐风楼碑录》。因罗振玉有非常活跃的收藏活动,故而看到的拓本版本和机会都多于同辈,不过他对碑文的考释是以郑文焯的研究为基础,刊正郑氏误释处八十多字(亦有误刊正者),并且将好太王碑的建立年代定位东晋义熙十年(开始罗氏认可陆心源说,后又推翻。),虽然在此前有王志修、荣禧等先持此说,但就考证文字来看,罗振玉的考证最为详实,远超前说。在陆心源定名基础上又认定好太王碑中『国罡上广开土境平安好太王』即是『广开土王』,依据《长数》考其干支,认定其在位二十二年。除此之外,罗振玉不单局限于一碑一石的研究,还用心收集集安出土的其他高句丽文献,对高句丽的历史学有推动作用,这种整体研究的思想值得后辈学者人人继承和发扬,比如集安还出土了『晋高句丽率善仟长』和『晋句丽率善佰长』两方古印,可知高句丽基础组织为什伍制度,带有军政合一的特色。正是罗振玉对学术的态度和推广热情,他的学生容庚也得真传,才有这套拓本复印件的因缘,其中原委可看吴瑾先生的前言。
我曾问过日本碑帖版本学家伊藤滋先生,他告诉我好太王碑的研究在日本十分火热,并分享了一些知识和信息,我随着其引导,对日本的研究情况做了大概了解。最早是在光绪十年(一八八四年),日本酒匂景信将双勾添墨本带至日本,引起轰动,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组织青江秀、横井忠直等人进行解读。五年后,日本《会余录》第五集首次刊登《高句丽古碑文》、《高句丽碑出土记》,横井忠直的《高句丽古碑考》和《高句丽碑释文》。之后日本菅政友在《史学会杂志》发表《高丽好太王碑铭考》,三宅米吉在《考古学会杂志》发表《高句丽古碑考》。到过集安实地考察的有鸟居龙藏(法国汉学家沙畹应该从日本了解到消息,比鸟居龙藏晩三年也到达集安考察)、关野贞、今西龙、黑板胜美、滨田耕作、池内宏、藤田亮策、梅原末治、水野清一、三上次男等,而且部分日本汉学家在中国考察时带有当时高级的摄影设备,应该在日本还存有好太王碑优质的历史照片,可惜我未能目睹。日本早期对好太王碑研究者都有明显的『皇国史观』,把当时朝鲜半岛南部诸国以及高句丽,都看作日本的臣民,以致大部分学者都将精力放在日本侵征朝鲜半岛这件事上。严重后果是出现权滕成卿伪造《南渊书》,以学术方式企图达到政治目的。

一九八二年新修碑亭

现状全景
早期学者对好太王碑的研究情况大致如此,希望更多人关注和参与研究,以学术为恒心,留下更多的史实成果。还有一部分对好太碑关注极高的群体,就是书法家,在吴瑾先生的前言里大略提到一些书法家的评论,因为其字体古朴,充满意趣。而至当代,越来越多的书法从业人员关注好太王碑,如此盛景,对于早期拓本的呈现、传承和对碑石的保护是如今的一个大问题。为了防止风雨侵蚀碑石,一九二七年,刘天成等人募捐修建碑亭,于一九二八年建成。一九六五年,国家文物部门派技术人员对碑体进行了化学封护。一九七六年秋,因碑亭长久失修,为防止发生事故,将碑亭拆除。一九七七年进行了第二次化学封护。一九八二年,当地政府扩大了遗址保护区,重建大面积围墙,同时重修碑亭,便是现在看到的样子。